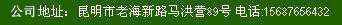|
即使一个非地图学领域的读者审视如今最常见的地图,也不难发现其最明晰的要素依次是国界省界、主要城市地名,其次才是交通网,再次是较浅颜色绘制的河流以及其他附属信息。而倘若翻看古代地图,主要的因素首先是用夸张的宽线条绘制的河道、主要山脉的分布、府城城墙及城内建筑示意图,其次才是州县名称大小不一的标注。这就充分说明古今地图绘制的用意并不相同,因此自然也就不能以现代精准性的眼光审视古代地图。倘若覆察《管子·地图篇》更便于理解古人对地图要素的审视。地图,首先是为军事服务的。因此它具备的因素便首先服务于战争进攻或防御。故其凸显“輏轩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可见,是否精准化复原地球地貌并不是古人重视的第一要素。 (嘉庆)湖南通志·舆图 本书题名为“非科学”,其暗含的旨趣与余定国(CordellD.KYee)一脉相承,一开始即针指李约瑟、王庸一系(此后还有陈正祥、卢志良、喻沧等人)视地图史为不断向科学化演化的理解路径,以及那些尊崇存在所谓裴秀“制图六体”或主观假象“记里画方”乃“标准化制图”的学者。开篇作者便径直抛出他的断语,即古代中国地图绘制并非是为了“将地球表面反应的更为准确”,而是有独特的功用。换言之,惟有剔除掉那种现代人以数据精确与否作为衡量古地图优劣的标准,才能理解古代地图。对此作者强调: 地图绘制的目的在于使用,而不是为了准确。从现存的地图来看,中国存在数量众多的附有大量文字的地图,这些附属于地图的文字中有很多是对地理要素的描述,例如道路的距离、山的高度等。从使用的角度来说,这些地图比表示了两点间直线距离的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更为实用。(制图六体中没有说如何在图中表示地形),因为使用这样的地图,行人由此可以判断大致需要的路程时间和决定每天住宿的地点。而当前保存下来的大多数地图都属于这种附有大量文字说明的地图,因此可以认为从现存舆图来看,“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不太可能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至少其不是中国舆图绘制唯一的一种传统或者理论。(p52)因此,作者进而否定古代存在一套按“制图六体”的标准化勘测绘制地图流程的可能。“制图六体”相传是晋代裴秀在绘制地图时的六个手法,所谓: “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据传统地图学史研究者所说,此后唐代贾耽、宋代沈括、元代朱思本和明代的罗洪先均一步步沿袭这一方法绘制地图。然而讽刺的是,如今却从没有一位学者能详细地阐述这六种方法如何在实际勘测中操作。而作者通过古籍库、方志库检索发现,其实所谓“制图六法”所设置的六个标准大致仅是一种理想化的诉求,而后凡称道六法者,大都仅略表尊奉裴司空开山之意,所谓的“六法”大抵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一样属于一种行业内的信仰。除胡渭等人略加注释外,大多数注疏的均仅祖述《晋书·裴秀传》,史源一致,故作者认为古代并不存在按照裴秀方法实际勘测数据绘制地图的史实。继而,作者受到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一文以及《九域守令图》题记中自叙曾参考《九域志》的启发,由此窥探到传统地图绘制应当是使用“极坐标投影法”,即“记里画方”。 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图》 “记里画方”说白了就是在常见的在方格网底本上绘图。据说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就是如此绘成“一寸折以百里”(一个方格代表一百里),因此被王庸等人表彰是继承裴秀制图六法的“分率”原则,是科学的比例尺地图。实际上,现存最早的方格图是宋代陕西省博和镇江市博藏《禹迹图》刻石。但作者认为,这看似是比例尺,实际上古人既不可能使用经纬度,更无法通过测量方向、高度、直线再逐步进行全国性的步步换算进行无法想象的大工程量绘图,且流传较广的朱思本《舆地图》和罗洪先《广舆图》是私人绘成,因此并不能操作。而较为可能做法是用方志的里程数据,然后数格子定位选点绘成。具体操作方法说白了没什么神秘的,比如《太平寰宇记》记载“长安(京兆府)东至开封(东京)一千二百七十里”,那么只需要在地图上以长安为坐标,向右数约莫十二个半的小方格写上“东京”就可以了。 《禹迹图》刻石拓本 在推想得出后,作者反复选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地图,以验证“计里画方”法在地图绘制中的实际运用,其实际做法如运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的数据来复原宋代《禹迹图》绘制的过程。其中基点的选择,如关西道为例,“一般是以某治所与京兆府的距离作为坐标,如果其与京兆府之间存在其他治所,则选择最近的治所作为基点。”(p89)通过在绘制过程中不断调整坐标,作者最终发现完全可以复制禹迹图,甚至连同失形的边缘也一脉相承。 又如明代《广舆图》,作者起先用《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的道里数据标注政区的坐标,但发现这两份方志数据太过粗略,由此作者认为《广舆图》有可能采用分省方志(如永乐《顺天府志》之于《广舆图·北直隶舆图》)以及隆庆四年()黄汴《一统路程图记》这类材料绘制。其方法依然是选定坐标,计里画方。例如绘制一幅《北直隶舆图》,只需要先确定顺天府的位置,然后再以顺天府为基点参考方志中记载某州距府多少里,然后按百里一个方格定位该州的坐标,并根据各属州之间的数据为位置进行调整,再以该州为基点绘制下属各县即可。换言之,具体操作并不需要任何运算。 禹迹图墨线图 山东地理之图 由此证明了古代地图应当是通过基层方志与各类当时里程书所记载的“四至八到”这类道里数据,层层定点绘成是一种想象的方位图。这便等同于说明,古人绘制地图本身便不是本于复杂运算后得出的地理位置实存而进行的还原,而是通过方志文字说明进行的一种坐标推测。而往往因为要融合几种不同的坐标关系,因此在操作中还需要进行主观的位置调整挪动。正如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所言“四至八到,方方凑合,求其毛发不爽,难矣。”况且府州县三层的数据,绘制过程中相当于先后重新设置两层基点,这就再次增加了不准确性。更致命的是,作者通过分析宋元方志发现“四至八到”这种传统舆图的数据并非是源于直线距离,而是本于实际道路通行的距离,而绘制地图时却无法呈现这种曲折性,因此错误可说与生俱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古地图的海岸线为何往往严重失形,山东半岛等主要地理图像为何往往被绘制成圆润的弧形边界,这正是因为其是基于零散的文字记载而定位的坐标距绘成。)简言之,“计里画方”根本就不算做比例尺绘图,最多是在绘制地图时画工用于参考纸上两点间距的一种刻度,其不仅无关真实地点分布的距离的等比例缩小,相反还往往掺杂进人为主观对地理坐标的移动。 言说至此,突然理解谭其骧的段子。据说建国初谭其骧绘制历史地图时,起初计划只是将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改正增补杨图显著讹脱之处,设想采用的今底图就依杨图底图的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只将图中清代的政区地名,改成五十年代的政区建制。然而稍后便发现《大清一统舆图》主要根据康熙、乾隆时期测绘的两内府舆图编制而成,与根据现代测绘技术所制成的今图相比,存在很大误差,要将清同治以后近百年改设的新政区地名及改变的新省界移绘到《大清一统舆图》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他坚决主张采用精确度高的今图作为底图。这一事件就足以证明传统舆地绘制方法跟现代的比例尺完全不属于一种手法,并非科学绘制,因此完全无法在其基础上增改,古今地图史并不存在沿承性。(参考谭其骧与《中国历史地图集》,《读书》年第1期) 河防一览图局部·镇江府部分 不过通过这一考察,虽然舍弃了民族主义地图史叙述的荣耀感,但相反,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古地图本身所负载的信息。譬如: 其一,虽然传统舆图目前看来并未能呈现政区分布实存,但是传统方志中记载的里程反而是当时最真实反映当时条件下车行或船行的数据,这恰恰是今日无法重新构想的。而这则是了解当时政令传递效率与疆域控制范畴的真实材料。 其二,通过这种不完美甚至是误差极大的地图数据,我们恰恰能够理解当时政府管辖的范畴边界,而地图上残缺的空白、未绘出的河流、数据不精的区域,恰恰表明当时政府有效管控的人口、税收、军备置防等仅限于地图标记处的地区。 其三,既然方志中所载的数据源于实际邮驿里程,而在主要物资流通地区河流作为主要的交通网络,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实际上应是以河道为纲,其次按河道的流经的里程一一附上行政单位所在。但事实却相反,如按作者操作,则是先定位好县级政区,再定位河岸海岸,最终描点成线。倘若如此,从河流实存到呈现为地图反而进行了两次数据转换,其准确度就大为折损,因此古地图中河流这一主要环节是如何绘制的则甚难理解。作者同样认为这是研究比较薄弱的环节。而古代地图几乎难见宏览式的交通图,在近代史学兴起后才产生严耕望、杨正泰等按数据史料重绘的交通网图,这就有必要重审古代出行或文书传递时人们头脑中真实的道路观念。而在具体道路里程测量中,从里耶简等出土材料中已不难看到,至迟于秦朝,政府已经有效掌握实际里程与当时条件下传递信息的时速,这具体又是如何测量里数的,同样值得深究。 金门图 此后,作者又探讨了城市地图画师绘制的意图。其认为“图中绘制基本上是与地方治理有关的内容,或者说城市舆图最初的绘制目的主要是为各级官方机构服务。”(p)而在第四章中,作者均围绕着城市地图绘画的目的进行分析。如: ·南宋淳熙八年()静江府城图,图上附有修成记,该图绘制时为抵御元朝南侵,故着重绘制军事设施,注重军事实用性。 ·北宋政和四年()《鲁国之图》据刻石所载,主要是考圣贤之轨躅。其目的则是为了教化士子,注重圣迹。 ·南宋绍定二年()《平江图》作者通过考察绘图主事者为平江知府李寿朋,继而索察李寿朋的事迹,得以在《吴郡图》中发现其曾对苏州的坊进行调整,复新建西库、南库、望云馆,因此得知该图的目的在于凸显子城。 在这种思路下,作者进而指出,除却传统直接想象到的图记、序跋有便于学者揣测地图绘制者的意图,更进一步指明,考察历史语境还可在方志中搜寻史料。这是基于作者的一种观点,即“方志图是为了便于使用者阅读方志,那么宋元方志编纂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方志图绘制的目的”(p) 譬如《新安志》序则说“夫所记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广远也,务知险易,不忘戒也。”又如《宝庆四明志》序说“观山川之流峙,则思为民行利”《景定建康志》序则说“地利明于形势险要之设”。最终,作者明确的抛出他的见解,即古代的地图,并不是为了对地理实存进行摹状,而是注重地图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无疑又暗合章学诚治教官师合一的精神。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到,作者在推测地图绘制目的时,往往参稽图记,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屡屡告诫的思想史手法之一,即章学诚所谓“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又如章氏提出应将著赋“详载于列传”,亦是强调文艺创作宜附载传记,以备后人洞察其创作旨趣。 读罢此书,尽管还有诸多疑问尚待讨论,譬如对于南部大量的水道交通殊乏讨论,不受省界限制的河流在古代如何测量绘制?方志中河流的支流与上流在古地图中往往缺略是否意味着无法航行?古地图中的山地绘制如何呈现和取择主要山脉走势和山峰?方志修纂与古地图配合后如何佐助施政者制定具体的政策制定?除城市地图外,全国性或省级别的地图如何呈现出绘制者的意图?在人口、赋税、土地等方面古地图具体又是如何与具体的鱼鳞图册相运用等等。但仍不碍于我们洞察作者的旨趣。 贯通全书,作者从一开篇先拿放马滩和马王堆这两套图所谓中国最古且“科学”的地图祭旗,到末尾对“四至八到”并非直线距离的考据。作者不断否定了前人各种民族主义情结对古地图“科学化”的吹捧。如果说上一代学者汲汲于如何凑合史料拼凑中国主动走向“启蒙”走向近代化的路径,那么该书的作者恰恰与之相背,其彻底扭转对晚近学者以“科学化”为鹄的阅读文本的视角,而在于提倡一种近乎历史语境学式思想史的知见,即理解古代地图,切记避免以现代人的视角矫强地审视其是否符合科学准则,而是要首先理解绘图之人的意图。正如作者所提示的: “地图并不等同于相片,不可能将所有地理要素绘制出来,因此在地图绘制时对绘图内容必定要有所取舍,但根本问题在于,绘图者对绘图内容取舍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绘图者要在地图中表现哪些‘权力、责任和感情’,或者更为直接就是这种选择所体现的使用目的是什么?”(p) 至此,我想读者自不难明白这正是我们思想史研究所奉行的教言,即“知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也是我们的准则,即以史解经,怀疑一切文本表述,文本必经过书写者行事予以推验,必须逆察作者的书写意图。如今治学,考验地是如何最大程度贴近古人活动的场域,而非自己悬空臆断一套道统沿承谱系。整本书质朴地复原地图绘制的手法,这恰是一个显明的思想史研究手法例证。 附:地图传抄渊流 明罗洪先《广舆图》——明新安朱绍本等编制《地图综要》——嘉靖四十三年()吴季源刊《广舆图》——万历本《广舆图》——万历汪作舟《广舆考》——明末吴学俨、朱绍本、朱国达《地图综要》——崇祯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天启程道生《舆地图考》——潘光祖《舆图备考》——美国国会《大明舆地图》(此后的几幅地图或更粗糙,或随意减少修改局部,这足以证明古人并不重视广舆图的准确性,其较为指明的原因在于其选取刻本易于复制。) 明罗洪先之前,可资其参考的全国性舆图还有明洪武二十二年()年《大明混一图》、明正德七年()《杨子器跋舆地图》、明嘉靖三十四年()年《古今形胜之图》、明嘉靖十五年()《皇明舆地地图》。 以上这些图很大部分可能渊源自元朱思本《舆地图》、元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和李泽民的《声教广披图》,乃至更早的宋代石刻《禹迹图》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万历癸巳()梁辀《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崇祯十七年()曹君义《天下九边分野人际路程全图》——康熙二年()王君甫《大明九边万国人际路程全图》——康熙十八年吕君瀚《天下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乾隆时期《乾隆今古舆地图》(此后几者都既不追求地图的准确性,也不讲比例尺,仅抄录地名。而其地图轮廓又均与嘉靖三十四年()福建龙溪喻绘制的《古今形胜之图》基本一致。) 作者认为,如果依科学性和准确性而言,大致只有康雍乾时期,采用西方绘图技术绘制了当时非常准确的地图,即《康熙内府舆图》《雍正十三排图》《乾隆皇舆全览图》,道光十二年()董方立、李兆洛《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光绪会典舆图》。此外,即使同时期的大量地图,均呈现出图中所绘道路距离同文字记注的距离并未能一一匹配。 摘录书单: 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读书》,7 马克·蒙莫尼尔:《会说谎的地图》商务出版社, 杨晓春:《混一疆理历代国度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初步研究》,《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凤凰出版社,年 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各省绘呈会典·舆图史料》,《历史档案》年第2期 辛德勇:《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九州》第4辑 《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首都博物馆藏舆图北京去哪里医院治疗白癜风最好宝宝白癜风能治好吗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趣味地理一张地图让我们换个角度看世界
- 下一篇文章: 年湖南省公考公告发布附职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