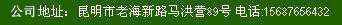|
文 李弘 ▲▲▲ 说了半天背景,又念了沉甸甸的圣旨,导游还站在景点门前热心介绍,大家却已急切地望着大门进口。现在,我们终于该进城逛逛了。
还真别说,如果没有向导的提示,我们不易看出一张城图与另一张城图的差异。几百年来的京城地图,都是同一张“凸”字脸,熟悉了,也感觉单调无趣了。《最新舆图》不但单调,而且得简则简。从南城的几张截图可以看出,上面的胡同街区,还不如《首善全图》上的详尽有神,四合院聚集的地方,连街道都懒得认真画直,更不要提看出地标性的建筑。
那么,这帝都,这张标榜“最新”的帝都舆图,新在哪里呢?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可以说,它就是有新意,就新在单调的圈圈围城中,冒出了几块翻牌儿的新政地标,它们正是我要去逛的地方。
晚清的十年,新政喊了十年,你要说一点改变也没有,也真是不公平。特别是在光绪、宣统换届年间,在圣旨的指引下,王公大臣们出了重手,改革官制,新部院代替旧衙署,废除科举,操练新军,修订法律,鼓励农工商,新气象可圈可点。连列强都注意到近来京城气象的温润,纷纷派员到北京当朝廷的顾问,帮助推进政策的实施。例如在如何集中控制铸币与银行这一项议程上,英国、美国和荷属巴塔维亚,三次派出高级代表来京,帮助设计中央银行的机构设置,稳定银本位的大清在金本位世界的兑换信誉。
任何改革的第一步,都要由新机构、新牌子打前站,跟着是人事任免,开张办公,尽管这些戏前锣鼓,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形式重于内容。但是,所谓改革,有时要的就是过程的隆重。新政时期的京城就是这样,又见“戊戌变法”时轰轰烈烈。只不过那时仅得百日,此番却经历了数年。时间的宽裕,足以使新政固化一些成果,新地标就成了其中抢眼的一大类。
《最新舆图》上北城详、南城略,从新政成果上看颇有道理。因为直到年,来自紫禁城的新政意图,集中体现在东城、西城的新地标上,基本没有崇文宣武什么事儿。更何况,在南城的胡同里,此时聚集着革命党与维新派的秘密活动,朝廷大员们深恐避之不及,地图上何苦要提及?
在东城西城找到这些挂牌儿新地标并不难,制图人便于看图人,把它们都涂成了桃红色。我想挑着说下面的几组,以偏概全,观察在一杆大旗下,京城在教育、军事、外交、工商等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这几组地标是,1)贡院与京师大学堂;2)兵部街与陆军部;3)总理衙门与外务部;4)大王府邸与实业学堂。两张与年的古旧《首善全图》上的对应片段,也被我裁剪出来,与《最新舆图》上的同一地点对对标牌。 1. 贡院与京师大学堂 在东城建国门内,正对着现在的古观象台,舆图上画了一红色的长方块,这里就是往昔学子们趋之若鹜的“贡院”。从明永乐十三年(年)开始到年,也就是说将近五百年,来自各地参加会试的考生,每隔三年,就要在这片天地里聚首一次,也叫“春闱”,为自己的官运整整禁闭三天。考上了就叫“进士”,也叫“贡生”,乡土小民便有了资格,马上致仕做官,把才智贡献给皇上的文官体制。放在现在说呢,这只是一个中等学位的考试,相当于今天的高中升大学的统考。北京举行统考,会设有许多考点,但那时全国就这么一个考点,同时能装九千考生应试,可见贡院入场券有极高的含金量。 戊戌年,选官要考八股文,成了变法“天字号”第一的攻击目标。耗到新政,取消科考的目标终于大功告成。是丙午年,皇帝有诏曰,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最新舆图》出现的年,贡院里举行了最后一场乡试。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俱往矣,一种官本位的教育将被另一个变种所替代。而红色的贡院,从此成了高墙围起的弃圆。年,占据北京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把贡院拆的七零八散。在西人镜头中,有许多落寞贡院的遗照,露出九千个鸽子笼的一角。我喜欢晒的是下面这张地图。这壮观的全景,是个形象写照,文官们的出身,怎样搭建了大一统皇朝治理的脚手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与有效延续,离不开人人机会平等的公平科考。英国哲人罗素曾说,学而优则仕的科考,优于西方中世纪通行的贵族世袭制度。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冲垮了贡院,催生新式学校。年也即是科考停止的两年前,大清颁发了圣旨,规定以后会考的贡生要想入职官府,譬如说当翰林院的编修、庶吉士,或是六部的中书,必须考一个“京师大学堂”的文凭,实际上是让新式教育弥补贡院身后的空缺,与传统官本位无缝接轨。学子们立刻心里明白,进士要不了两年,就贬值啦,要想涉足政坛,报效国家,必需寻找新的晋身阶梯。那么,到哪里去上这座新式学府呢?往景山东面一望,有一红色方块,面积约有贡院一半那么大,赫然写着的就是“京师大学堂”。它的前身是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后世即是名声显赫的年国立北京大学。戊戌变法的高潮中,25岁的梁启超为它起草了一份章程,亦获得了光绪的批准,中国现代教育因此产生了第一份学制纲要。 年时,大学堂已经分设十三学门,包括诗经、周礼、春秋左传(经科);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文科);政治、法律(法政科);银行保险(商科);农学(农科);地质、化学(格致科);土木、矿冶(工科)。其实,此时的大学堂根本没有舆图上那么大占地,它的几个院校也不在景山附近。绘制者这样画,用心是想突出它在新式教育中的真实地位吧?
20世纪初年的年轻人,上不了京师大学堂,也不要紧。在舆图上还标出了一块一块红色,它们是法律学堂、陆军小学堂、实业学堂、艺徒学堂,等等。风声雨声读书声,国事家事天下事,声声事事,从此不要去东城的弃圆找寻,新式学堂向一代学子敞开了大门。 陆军部与兵部 兵部是朝廷传统的御用军事部门,与其它五部一道,取址于千步廊的两侧。廊东有四部,吏部、礼部、兵部、工部。年以后,公使馆挤走了许多衙门,在洋圈圈的西墙给朝廷留出了一条街,叫“兵部街”,留的正是这座衙门的面子。 第一场鸦片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的八旗制度与兵部设置,根本不可能与洋枪洋炮对峙。到曾国藩打太平军,湖南建了“湘军”“水师”,兵部在国内战场上也成了摆设。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上呈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清廷开始效法英国,先创设皇家海军,即北洋舰队。中央的“海军衙门”,又拖了11年才在北京成立。据周馥在《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的考证,衙门成立之初,连办公之地都没有。怎么办呢?就借了大清护卫京城洋枪队“神机营”署内的空闲房间,稍为修葺,将就做了都办府。《北京晚报》08年8月28日有载,这神机营的位置,大概位于后来的煤渣胡同,医院的北侧。这个委身于人的衙门很短命,前后只存在了10年,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它就被裁撤,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还没有找到一张帝都地图,宽大为怀,为这个衙门留下一滴墨迹。
大清搞不定海军,还是回头搞陆军吧。陆军部是年成立的,同年裁撤了兵部,为御用军事指挥画上了大半个句号。陆军部没有像海军衙门那样委屈自己,也不想与老式衙门为邻,它在东城区的铁狮子胡同3号,就是后来的张自忠路,兴建了东、西两组洋式砖木结构小楼,西部为陆军部,东部为陆军部培养军官的贵胄学堂。《最新舆图》上陆军部地盘很大,锐气张扬。 陆军部成立之初,并非是国家军队,但这是中国军队走向国家化的第一步,但是迈的跌跌撞撞。它取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建制上,如传统的武科考试被彻底摒弃,以前的军武将官全都靠边站,冷兵器扔进了垃圾堆。陆军部训练的是西式军队,效法西式组织,听命于新式统领。先行一步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成为陆军部的栋梁。其次,大清学习了日本,搞起了义务兵制,名曰保卫国家。法律规定,20-25岁的年轻人必须服役,正规役或预备役,平民百姓的孩子,也有进入陆军学校的机会,接受现代化的军事训练。
陆军部是京城的第一座“军队大院”,年,在这座院子里又挤进来重新恢复的“海军部”,大清的军事建制趋于完善。不过说句实话,无论是陆军部还是海军部,它们彪炳青史的一页,不在扶助了满人朝廷,也不在保家卫国,而是在民国初年制造了北洋政府,上演了长达十几年的军阀混战。
新政中央行政体制改革,陆军部是一个突出代表。从年到年,大清把承传了几百年的六部,陆陆续续改成了十一部,名字叫的我们越来越熟悉,好几家都在舆图上标了出来,尽管面积没有给予同样的强调,也都被涂上了红颜色。例如民政部,占据了旧日的“护统”,地点在沟栏胡同,后改叫“民政部街”;外务部,是总理衙门的翻牌儿;度支部,印章用的是原来皇家的户部,用的也是户部的旧址;法部与高等审判,牌子底下盖着刑部,督察院与大理寺,仍守在千步廊的西侧;邮传部,利用了皇城西南角外“段家坑”的一片荒地夹道。随着新机构的出现,军事与行政部门就不再囿于皇城内,小胡同中走来一批批新的大员,先称尚书侍郎,再称大臣,副大臣,最后变成了总长次长。他们相见的礼仪,也不再是点头抱拳,而是顺手递上一张小小的名片。
3. 总理衙门与外务部
北京有一条不平常的胡同,叫“东堂子胡同”。第一它的历史很长,元代就有记载,而至今仍安然躺在那里,前后总计快有年历史。第二它是第一个对外开放衙门的所在地,也是第一个现代部委的所在地。第三这里的大员一跺脚,总是踩在大清最敏感的神经上。所以,我们不妨在这里流连一会儿。 据说由于这条胡同与另一条胡同重名,所以改加了一个“东”字。在这两张老旧地图上,它的名字还没有改。年签订《北京条约》时,额尔金强令恭亲王同意,设立常年办公的外事部门,及时解决外事纠纷。这个衙门不能离皇宫太远,也不能离公使馆太远。找来找去,就在东华门外找到这么一片闲置的院子。它原来是大学士塞尚阿的宅邸,后来充公,做了铁钱局公所,大清末年成色低劣的铁钱币,可能不少就流出于这座院子。改成“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后”,大宅门又拓宽加高,让跨进门栏的外国人不敢轻视咱大清的国威。
上面的两张图,可以看出两个差别。其一,是右面那张图上既有“总理衙门”,又可以看到“外务部”的名字。其实这是不对的,外务部出现的时候,总理衙门必须摘牌了。其二,在堂子胡同的西口,多了六个字“石牌楼克林德”,这是庚子之变后,大清朝廷被迫树立的牌坊,以表达对义和团杀害的德国公使的歉意。
总理衙门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没少发神经,也导致大清最后的发疯。当时的外务大权由端郡王载漪把持,他又是伪造文件,又是操纵义和团,最后鼓动慈禧与列国彼等开战,干的净是荒唐事。年,西方列强惩罚了载漪父子之后,还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求关闭总理衙门,彻底更名换班设一个新的部委,名列中央六部之首,而且薪饷要最丰厚。在老外的心里,衙门这个字,寓意明确,就是王大臣或军机大臣为皇家打工。改成了外务部,好像它就有了更大的独立性。新政的其它机构设置,大名叫起来与六部不同,都强调了是大清政府而非皇家的行政部门。其实这仍是自欺欺人。政体未改,没有内阁,也没有政务院,那里来的政府? 公平地说,就算是皇帝的外府,总理衙门或外务部在“皇圈圈”的权限内,还是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包括开放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又监管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推动了国家的进步。年,外务部还设立储才馆,培养专业的外交人才。年,外务部游美学务处筹建的游美肄业馆,即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年以后,外务部又一次改名,叫“外交部”了,它往南迁了一条胡同,图上显示的石大人胡同,画了一个红块,好像就是为它留的。此街后来改称为“外交部街”。中文里,我们似乎体会不出名字有什么差异,英文听起来就不同了。“外务”是管外事的(affairs),一时一事,短期目光;“外交”(relations)是管关系交往的,是长期的战略的考量。从那时起,这个部委没有再改过名字,陪伴着中国走过了过去的百年。
最后,我把图上剩下的红色块过滤一下,发现大块的还有两类机构,即,
4.大王府邸与实业学堂
清末城里的大王府在东城西城是比较均衡分布的,《最新舆图》上只点出了西城区的王府,包括恭王府,庄王府,礼王府,定王府,郑王府,顺成王府,郡王府,豫王府,等等。这等王府的主人,不是左右晚清时局的一等人物,也家世显赫的贵胄爵爷。为什么要在舆图上突出标示这些王府,而略去了另一些?这些恐怕与制图人的定见相关。
西城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片红,那就是实业学堂、艺徒学堂,它们的占地超过了任何一座王府,相信亦是制图人的定见在背后鼓动。这是两座什么学堂?为什么没有建在南城,那里是匠人作坊集中的地方,而选择在贵胄云集的西城?它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企业家,后来出了一些什么人物?对此我的调查还很不到位。我只是相信,很可能是新政人士明里暗地扶植了它们,才可以这样堂而皇之上了地图。我也有个推测,两所学堂在这样的氛围下,经历过一段繁荣,造就了京城第一代的工人阶级。 这四组地标看下来,我不由得对两位制图人肃然起敬。他们下了决心,不管新政今后遭遇什么困难,哪怕是中途夭折,一定要把翻了牌儿的地标刻在城图上,刻得很清晰,刻得很高调。他们就想要人们永远记住,当年的改革是真实的。假以时日,大清一定有救,中国一定也有救。
但他们的想法,和历史反复证明的变革规律有些相悖。许多学者们总结说,如果专制政治绝不放松,改革是没有机会突破旧制度的藩篱,结果或是行之不远,或是南辕北辙。大清的新政,本以为是可以将革命冲进下水道,但事与愿违,这么多的新机构,新地标,渐次开启了“国家政体在民”的意识。许多海外留学生,年富力强,回国后,正好新机构在招手,便担当起行政的实权人物。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他们日常工作的实际效果,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蹲在大清的城墙上“拆砖取土”。
然而,决定大清与中国命运的力量,此刻并不在京城,也不在新设的部府。舆图的作者冥冥中似乎也感觉到了,南方各省的大地上,已经铺满了抗命起义的干柴。只等着朝廷擦一根火柴,干柴就会呼啦啦燃起来,星火燎原。地图没有忽略地方与中央对抗的形势,它用外省驻京会馆的信息,把我们的目光从新政的地标,吸引到各省咨议局议员在京的组织与活动。 作者为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 专栏近期连载中: 舆图出自谁的手: 他希望看到光绪开拓的事业后续有人,拿八月初一日的“通谕”真当回事。起码,他相信皇历上还会有宣统九年,将来,会有大清皇家议院开张的那一天。 光绪皇帝有话要说: 别看那么多圣旨,其实都是装装样子,朝廷从来没有真心诚意想过让权。君主立宪不过是在地图上的逛街,手指滑得挺远,脚底下其实没动地方。 学了西洋学东洋:用各式各样的印刷品来为改革摇旗呐喊,诠释朝政的意图,在中国在外国,在前朝在现代,不乏先例,但《最新舆图》仍然让人耳目一新。 没有天际线的大村庄: 天际线圈出的空间,是市民工作生活与娱乐的公共空间。而中轴线圈出来的土地,是皇帝和王公大臣的领地,是一统天下建筑理念的辉煌。想想两条线的差异,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游客还是京爷都会认同,清末的北京的确落伍了. 洋路牌是生不了根的: 洋名路牌树错了地方是生不了根的,最终要被本土文化的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不成气候的金融街: 这条商业文化浓厚的小街,十九世纪晚期涌来了一波金银潮,不是来自达官贵人的参差宫殿,而是来自西方的商业银行。 百年前这里叫玉河: 老外们过去吃过天高皇帝远的苦头,早就悟出来,圣旨出了京城两里地就要走样。我们就要住在二环内,就要在皇城脚下,与五府六部的衙门为邻。 洋人到北京,皇上去山西: 精明的买办早就料到,清军绝不是洋人的对手,英法早晚要打到北京。但是皇上也绝不会放下“天下独尊”架子,和洋人坐下来为原则讨价还价。 :北京的冬天冷得紧呢: 这句话,是乾隆内阁大学士和绅,提醒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噶尔尼勋爵听的。在使团团员的眼中,泱泱东方大国是头号大市场,富足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消费者。他们需要摸清楚一个国情,也是一百多年前荷兰人没有回答的问题,即开放了的中国人需要什么? 洋人地图里的中国帝都: 几百年前,地图上的信息就意味着情报,地理知识的保密犹如保卫今天的网络安全。没有地图,洋人就找不到进入帝国心脏的大门,起码,朝廷里有些人就是这样认为。 旁观中国由财新传媒出品,其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财新传媒及/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 2017治疗白癜风最好的药哪里能买到北京白癜风治疗要花多少钱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hunanzxsheng.com/hnlt/7387.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重磅调查中环联都挂靠,环保部怎么管
- 下一篇文章: 湖南关于组织开展2017年度土壤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