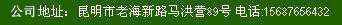|
按:今年夏天,母亲生病住院,在医院陪护母亲的日子里,听她讲了一些往事。母亲出院后,我回家看望,听二老讲了更多的家史。乃翻出几年前所记双亲之口述,再作增补,为父母亲多舛、隐忍、不屈、自强、存爱的人生、也为我家开枝散叶的过程留一组底片。 一 我的祖父名叫孔炳煌,生于年,是孔家第73代孙,庆字辈,他从小就住在长沙县黄花(公社、镇)新湘(大队、村)南薮塘,是家中八个孩子中的老满。他的母亲4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父亲也在59岁的时候驾鹤西行。就在他的父亲去世前,家里为了给病人冲喜,让他将同为17岁的方桂成娶进了家门。但我祖母进门并没能挽留住老公公的性命。于是,爷爷和奶奶独立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爷爷很能干,不仅家事料理得很好,还担任了甲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我的父亲孔三明生于年11月,繁字辈,他是爷爷奶奶的次子,在他之上,有兄长孔汉明,在他之后,有妹妹孔再明、弟弟孔忠兴相继问世。父亲出生在日寇侵华的战云中,那一年长沙大火,民不聊生。幸亏前三次长沙抗战没有打到长沙县,四岁以前的父亲得以在家中安享童年,但四岁的时候,他终于不得不跟着大人在兵荒马乱中东躲西藏,在亲眼看到一些邻里亲朋被日寇残害的情况下,侥幸活命。 由于爷爷和奶奶持家有方,他们渐渐累积了一些家底,年迁到廖家冲,置了田土和房屋。但爷爷对教育不是太重视,他的儿女都只准读5年书,他认为他自己只读了5年书,就能够很好地掌管家事,儿女们读5年书足够了。我父亲6岁半开始读私塾,跟过三个老师,从三字经、百家姓读到春秋、左传、古文观止,到年结束,刚好5年。父亲好学认真,成绩列同学前茅,但因为家庭缺乏劳动力,爷爷让他辍学放牛,同时做附带劳动力。 祖母晚年在我家屋前。 新中国成立后,年进行土地改革,对农村家庭进行阶级成分划分,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之分。中农当中,又分为上中农、自耕中农和下中农,上中农又叫富裕中农。上中农和下中农的区别在于农田的耕种请不请人,上中农家庭田地较多,自己耕种不下,所以要雇人,下中农家庭田地较少,不够养活自己,要到富裕人家找活干。量化起来,就是上中农家庭年收入的25%是由雇佣农民创造的,因此被认为略带剥削。那时候,我爷爷奶奶有耕地10亩,有耕牛,生产资料齐全,被划为上中农,也就是富裕中农。 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粮食全部由政府统管,作为均贫富的手段。于是,所有田土和粮食富裕一点的农家,家里的粮食都被搬空了,爷爷奶奶一家五口靠种荞麦、萝卜当粮食。年冬组织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又一次在土地和生产资料上均贫富,农家的耕牛、农具都以低价入社,逐年偿还。粮食分配则根据社员的工分来定,基本口粮一般为人均斤谷左右,加上工分分配,人均在-斤谷之间,这个量只够基本活命。年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家的生活并无改善。 年国家搞大跃进,农村搞大食堂,所有人凭饭票在食堂吃饭,好多人吃不饱。那时候国家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阶级斗争态势严峻,人人自危,富裕中农这个家庭成分让爷爷和父亲得小心做人。年-年,中国处在更加凄苦的困难时期,全体过苦日子,人均口粮越来越少,人人处在饥饿中,很多人不得已挖树根、野草充饥,水肿、白喉、麻疹等疾病流行,食堂里经常死人,一些青壮年开始跑江西等地逃生。 尽管生计艰难,但年轻的父亲在那些年有自己的乐趣和成就感。他天资聪颖,虽然只读了5年书,但自学能力很强,读、写、算俱佳,同时,他身材高大,性格宽厚,能说会唱,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他年起在初级社担任记工员,年-年担任初级社的信用社会计,年-年担任大队会计及资料员。但从年起,阶级斗争越发激烈,因为家里的阶级成分问题,加上爷爷是国民党员这一历史问题,父亲在政治上被排挤,他没能继续在大队工作,而是回生产队劳动。屋漏偏遭连夜雨,相恋几年的女友也无情抛弃了他。 父亲在大队担任会计的时候,有一个姓粟的姑娘在大队幼儿园担任老师,他们两人都在队部做事,男才女貌,十分般配,在大家的撮合下,顺理成章地谈了恋爱。两年下来,准备结婚了。这时候,那姑娘的姐姐对她说,妹啊,你跟孔三明好是好啊,不过你是贫下中农,是共产党,他们家是富裕中农,是国民党,不要到时候一起受整啊。一句话就把姑娘点醒了,当即决定分手。父亲因此受了很大的刺激,心里痛苦,身体也出了问题。他频繁咳嗽,痰中带血。 二 我母亲叫刘应双,年11月出生在离廖家冲不远的虎塘,是外公刘仲国、外婆陈仲莲所生的8个孩子中的第二个,是长女。刘家是个传统农耕家庭,以勤劳节俭闻名于四乡,土改中定的阶级成分是自耕中农。母亲7岁入读一个叫杨家湾康来小学校的新式学堂,聪颖上进,很爱读书,但被农家重男轻女思想所害,只读了三年书就被外公勒令休学,回家学习纺纱和针线活,参与田间劳动。母亲12岁的时候,家里安排她去学织布,跟着师傅学了一年就出师了。外公给母亲制了一套织布的家什,母亲独立上门为别人家织布,母亲手巧艺精,肯吃苦,誉满乡里,一年四季都有人请。一幅布一般是三丈二尺长,两尺四寸左右宽,母亲手脚飞快,一天至少可以织下一幅布,有时候起早贪黑,甚至可以织下两幅。 以粮为纲的农业合作化生产开始以后,本地就不再种棉花了,流通也受限制,外地的棉花进不来,织布行业日益萧条,母亲上门为人家织布的机会越来越少。年,合作化进入高潮,所有行业都纳入合作化集体经营,刺绣是其中一个集体项目,一批年轻姑娘当了绣花姑娘。母亲于是在年开始学绣花,也是一学就会,一个月之后就开始带徒弟。绣花是一个集体工作,母亲先后在本地桐庐、北薮、茶塘等湘绣组、湘绣厂绣花。农忙时节,湘绣厂放假,母亲则回队参加劳动。绣花的酬劳,大部分体现在队上的工分中,个人可得微薄的工钱。绣了几年花得来的工钱,母亲没舍得用,都在一个存折上面,存折连同她的名章一起藏在家里衣柜抽屉的夹层里,这个是要存着将来添置嫁妆的。到了要用钱的时候了,母亲去找存折,结果什么都没找到。家里的屋翻修过几回,到底是搬家的时候家里人没留意把存折弄丢了,还是什么人瞒着她取了钱用了?母亲始终没有得到答案。 图片来自百度。这样的绣品,母亲做过很多。 母亲身材不高,但做事霸蛮,吃得苦,粗活细活都不落后。16岁的时候,她一人可以背一个重达多斤的三人车水槽,见到的人无不惊叹。车水的时候,第一级水槽最低最平,踩车最轻松,第二级往高处走,更费力一些,第三级更高更陡,也最费劲。开始的时候,大家看母亲个头小,把她安排在第一级,后来看她人小力气大,就调到第二级,最后居然让她去踩第三级,水槽几乎是竖起来的,这样的重活,母亲没少干。母亲是家里的长女,下面弟弟妹妹一个接一个,外婆对母亲说:应双啊,你是大的啊,没办法啊,一屋人穿鞋袜要靠你啊。20来岁的母亲每天从湘绣厂下夜班回家后,还要在煤油灯下为全家人纳鞋底、缝袜底子。 年,父母亲都23岁了。一个未娶,一个未嫁。我奶奶找到我母亲的小姨,请她为我父亲和母亲做介绍。其实所谓介绍是一种程序,因为大家都认识。我外婆和我奶奶两家相隔不过一里地。我外婆怀我母亲的时候,我奶奶怀着我父亲,她们聊天时,就曾打趣说如果生下来是一男一女,就结儿女亲家。后来生下来果然是一男一女。不过两个年轻人看起来有些差距。我父亲1米8的个头,仪表堂堂,我母亲1米55的身材,普普通通。我父亲书读得多,才华出众,我母亲只读过三年小学,虽然会织布会绣花,能吃苦能干活,只是一般的农家女。指腹为婚的事情,很多年里没人提起。 现在人家来提亲了,我外婆就把这桩陈年旧事向我母亲说了。但是我母亲不同意,因为她知道父亲和姓粟的姑娘谈恋爱又被分手的事情。人家不要的,现在要她接手,她心里自然不乐意。同时她也是有人追求的,并非嫁不出去。我外婆尊重我母亲的意见,随她自己决定。但是我外公冲他女儿一顿吼:你还不要人家,人家哪点配不上你?人比你漂亮,书读得比你多,家里屋都有三进,你还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家? 母亲一方面被她老爹质问,另一方是面临父亲急切的追求。父亲有时候守在外婆家里,有时候守在母亲从别人家织布回家的路上,送书给她,写诗给她。两方合力,使母亲招架不住,三个月之后,结婚的事情就定下来了。母亲后来说,父亲这边把他生病的事情瞒得太紧了,她完全不知道她的未婚夫咳血,她要是知道父亲是这个身体状况,这个婚是无论如何不会结的。 结婚45年后的父母亲。照片摄于长沙黄兴路。 三 年农历9月27日,同年同月出生的父亲和母亲结婚了。那一天是公历10月10日,也就是双十节,爷爷是国民党员,觉得这个日子好。集体食堂已经在当年的4月解散,喜事就在家里操办,处在三年天灾人祸的最后一年,农村经济崩溃,物资匮乏。总共只买了10斤猪肉、几条咸鱼,萝卜入席,淡酒待客。不过生产队破例发给一张布票,父亲揣着这张极为珍贵的布票,走到几十里外的春华山,扯回一段灯芯绒布,给母亲缝了一套衣服做新娘装。当时正值秋收,结婚的第二天,母亲就下田扮禾。从此后,脏活累活,从不捡易丢难,白天出工,晚上绣花。 合作化结束之后,绣花是一种个体劳动。接花和送花要到榔梨或长沙丝茅冲,全靠两条腿走,并且是山间小路,母亲每次都是天刚蒙蒙亮就出发,走到长桥天才大亮,晚上回到家则天已断黑。母亲每天挑灯夜战,一般绣一个被面要花一个月功夫。送花时,厂里根据绣工的好坏评定等级,付给几十元的工钱。从年到年,母亲绣花的工钱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 父母亲一共生了5个子女,除第二个初生即亡外,其他4个子女均健康成人。长女小玲生于年8月,二女小献生于年2月,儿子朝晖生于年10月,老幺,也就是我,生于年正月。我的出生可谓阴差阳错。母亲生下我哥哥之后,本不想再生了,因为孩子多了,负担很重。那时候政府已经开始号召计划生育,所以母亲发现怀孕之后就准备去“刮毛毛”,怎奈那时候做流产手术很不方便,需要跋山涉水医院。医院,走到水渡河,才知道因涨水根本无船过河,没去成。医院,却被医生告知,毛毛已经长大,不能刮宫了。母亲无可奈何生下了我,我的命就是年的那场大水保下的,母亲因此经常说我命大。 全家福。摄于年中秋节。 父母亲于年秋结婚后,和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姑姑、叔叔等组成一个大家庭。父亲的病在那一年中更重了,年甚至有时候大口吐血。那时候大家觉得这是痨病,可能治不好,母亲既焦急又后悔,她觉得自己被骗婚了,想要离婚。但是婚不是那么容易离的。母亲一方面要照顾羸弱的丈夫,同时第一个孩子又呱呱坠地了,生活得痛苦不堪。父亲在生病当中,做不了重活,挣到的工分很少,却对文艺发生了兴趣,自学了一些文艺知识,开始诗词、曲艺创作,参加队上的宣传工作。 大伯在关键的时刻支持了他弟弟。那时候家里养了4头肉猪,大伯对爷爷说:这四头猪不准拿来做其他任何事情,就只准拿来给三明整病。到医院一检查,父亲得的是肺结核。医院用的药是链霉素。父亲连续打了一个星期的链霉素后,咳嗽就好转了。父亲得肺结核的原因,除开之前被恋人无情抛弃造成了身心创伤之外,可能还和长期营养不良有关。母亲说,为了给父亲调养身体,她听了别人的建议,把肥肉切成块,装在罐子里,放在火里煨,煨好后的肉实际上是粘稠的油,她奇怪父亲居然也能吃下去。 父亲身体好转后,从年开始又重新参加生产队的管理,参加了修河、造林等大运动。父母亲又添了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出生三天就死掉了,第三个孩子是女孩,也就是我二姐。伯父母也添了两个女儿,大家庭因此人口众多。同居一屋,同桌而食,妯娌之间,难免碰碰磕磕,生出一些闲气。精明强干、12岁即到孔家来做童养媳的伯母让母亲受了不少委屈。伯母到孔家时,伯父才13岁。伯父17岁即参军离开了家,所以伯母和奶奶之间的感情如同母女,在家事摩擦上,奶奶偏袒伯母一些。 母亲在精神上压抑的同时,身体也出了状况。她在年怀着我哥哥的时候,得了严重的皮肤病,全身皮肤溃烂,缺医少药,却不得不带病劳作。母亲每次回忆那段日子都眼含泪水,为大家庭里的其他人对她的嫌弃甚至放弃,为附近的赤脚医生断言她得的是绝症。有一次,母亲在我小姨的陪同下外出诊病,乡下医生没有给她做皮试就直接注射青霉素,药物过敏的母亲在回家的路上,全身肿起来,天黑时分倒在行人稀少的山路上,几乎断气。母亲对她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说不清楚,但她确定,救她的药是灰黄霉素!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建议她吃这种药,但这种药的副作用特别大,母亲顾不得那么多,吃了一瓶,缠了她三年的皮肤病竟然真的断了根。 四 年,大家庭一分为三:伯父伯母带着两个女儿、父亲母亲带着三个儿女、爷爷奶奶带着忠兴叔叔。分家之后,父母亲在精神上要畅快一些,但生活上的压力如影随形。年,母亲又生下了我,我的出生,意味着父母亲两人劳动,要养活全家六口人,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家里时常两三个月不买肉,虽然猪肉的价格每斤只有6-8角钱,但折算起来,是一个劳动力两天的收入。所以,只有在插秧收谷、过年过节或者有重要亲戚上门的时候,家里才称肉改善伙食。买肉也很不方便,父亲在天没亮的时候就要出发,走8里地的路才到,之所以要赶早,是因为排在队伍前面才能买到肥一点的肉。人人争买肥肉,则是因为那时家家的菜里都没有多少油,对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吃油的问题比吃肉的问题更迫切。 年,母亲到省妇幼保健院做结扎手术,带了几斤鸡蛋进城补身体,医院,有人要买鸡蛋,价格又好,母亲一个都没吃,全卖了,卖鸡蛋得来的钱,扯了一块布,给两个大女儿一人做了一件红褂子。之所以如此省俭,实在是因为家里经济拮据。父母亲整日在队上出工,只能换回一家人的口粮,但家里除了吃饭,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吃油盐、孩子的学费、一家人的衣服、添置日用品、送人情等等,全靠母亲养猪积累一点钱来计划用度。那时,南瓜是主要的家常菜,因为南瓜不用放油也可以煮着吃。有一次,我家附近有一口水塘干塘,捞上来好多鱼,父亲看着鱼很新鲜,想全家人改善一下伙食,就买了一条2斤多的鲢鱼回家。到了家,母亲看到鲢鱼,心痛又生气,一定要父亲把鱼退掉,理由是家里条件不好,没资格吃鱼。鱼后来还是没有退,一家六口一起吃了,鱼肉鲜美,小孩子高兴,两夫妻却不高兴。 父母亲每天出集体工,我们几个小孩子没人料理,只能让大的带小的。母亲说,夏天的傍晚,当她收工回家的时候,会看到几岁的我靠在屋门口的门槛上睡着了,脏兮兮的脸上沾满苍蝇。因为要抓紧准备一家人的晚饭,她往往到门前水塘里挑一担水,倒到脚盆里,让比我大8岁的姐姐给我洗澡。 年,长沙县组织了一批农技员到海南省三亚市育杂交水稻种,每个公社派一人,父亲作为新湘公社的农技员名列其中。育种时间为期半年,年11月9日至年5月13日。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母亲不得已承担了家庭男劳力的所有工作,包括外出买猪,挑谷打米等。母亲之前从来没有赶过猪,但她硬是从离家几十里的地方买了一对几十斤的猪赶回家,几十里小路,从下午到晚上,爬坡过桥,一路上所担的心、所受的累,现在回忆起来她仍是一声叹息。挑谷打米在那时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整个大队只有一个打米房,人多拥挤,因为机器不停,灌谷子、接米、接糠几个环节得手脚非常麻利才不至于和前后家发生纠纷。因为白天要出工,母亲只能晚上挑谷去打米,十来岁的姐姐跟着去做帮手,路远难行,在排队的时候又常受到其他壮男排挤,母女挑着米和谷糠回到家时,常常已是半夜。 父亲种的红薯。照片摄于年11月。 那时候,队上分的粮食不足以全家吃饱,所以红薯是我们的主食之一。当年的红薯品种还未改良,白色,个头小,多筋。红薯当季的时候,饭里面一半红薯一半饭。不当季的时候,母亲也会把之前晒干收起来的红薯丝放到饭里面一起蒸熟,还是一半红薯一半饭。早餐通常都是红薯粥,红薯是连皮蒸的,熟后在锅里加水和成糊糊,无盐无糖,哥哥实在吃腻了,宁愿空着肚子去上学。不光红薯皮不浪费,茄子也是连皮蒸着吃,或者带皮切碎炒着吃,甚至有一个菜是茄把子炒辣椒,茄把子就是包在茄子一端的花托。父亲从海南学习育种回来后,加紧组织本地育种,推广新品种、新肥料、新技术,为提高我们大队的水稻产量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年,6岁的我已经开始记事了。除了记得父亲从海南带回来的各种海螺、贝壳和椰子,更记得因为没有白衣服而好一顿哭。有一天,队上的广播突然不放我能倒背如流的打铜锣和补锅了,反复放一个我没听过的曲子,大人说那是哀乐,毛主席逝世了!跑到队部一看,密密麻麻的人挤在礼堂里开会,都穿着白衣服,胳膊上带着黑袖章。我又跑回家,找母亲要白衣服,母亲从屋前的水塘洗衣服回来,一边往竹篙上晾衣服,一边对我说,没有白衣服,穿浅色的也可以,但我不信,大哭起来,因为没有白衣服。 我小时候的衣服大部分是黑色的,母亲先织出白布,染黑,再请缝纫师傅做成衣服。屋门前水塘边的灌木丛上,经常晒着刚刚染过的大幅黑布,家里则经常响着织布机的声音。那时候,母亲除了织较厚的白色土布,还织一种较薄的浅色麻布,那是用来制蚊帐的。有一次听母亲对父亲说,要给每个女儿制一床蚊帐作陪嫁,有空就要抓紧织。麻布来之不易,包括打麻、剥麻、沤麻、柔麻、撕麻、缉麻、织麻等多道工序。队上集体种的苎麻分一些给各家,父母亲将麻的韧皮从麻杆上剥下来,再刮掉表皮,放到水里浸泡,又放到锅里煮,晾干,将麻纤维分离,再将麻丝缉成线,最后织成布。夏天的夜晚,蚊子很多,母亲穿着深筒套靴缉麻线,为了赶工,她顾不上热。明朝王冕《江南妇》一诗中“日间力田随夫郎,夜间缉麻不上床”是我母亲当年的真实写照。 图片来自百度。母亲缉过无数这样的麻线坨。 五 年,我入读东春小学,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准备白衬衣参加集体活动。那天天气很热,我走到烟熏火燎的灶屋告诉母亲,母亲在灶后面探出头来说,已经请后屋的刘裁缝去做了,明天就有拿。想着自己可以穿着白衬衣站在整齐的队伍里,我感觉生活一片光亮。更大的光亮来自家里砌的新屋这件大事。父母亲年从爷爷奶奶的大家庭里分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以及其他几家都还是挤住在老屋里,房子窄小且不就用。现在,父母亲节衣缩食攒了一点钱,在老屋东边百米远的竹林旁开出了一块新屋场,砌了长沙农村最常见“五间头”,说是五间,其实有七间,中间三间正房,东西两边各有两间耳房。虽然是土砖瓦屋,但房子周正紧凑,阶基宽敞,在七十年代末的农村,可算气象宏伟。 砌屋的土砖是父母亲在屋前的田里挖泥巴做的,湿泥巴做砖,在大太阳下晒干再挑到新屋场备用。土砖又大又重,一只箢箕只能装一口砖,父亲一担一担地挑。瓦要用特殊的白泥来做,取瓦泥的地方离我们家有五六里地,父亲用独轮土车一车一车地运泥回来。土车上坡特别费力,父亲在车前绑一根麻索,前面的人拉车,父亲掌车在后面推。我跟随父亲去拉过车,下坡的时候,如果路陡而不平,稳住车不栽不翻很不容易,走在前面的我很怕车子窜到我身上来,惊心动魄。瓦是请瓦匠做的,泥瓦干透后,父亲又请人做窑烧瓦,如果窑不好,也就烧不出好瓦,意味着前功尽弃。在准备砌新屋的各个环节,从做砖、做瓦、烧窑、挖地基等等各个环节,父母亲都高度戒备,全力以赴。 父亲的弟弟于年因病去世了,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伯父一家又常住湘潭,我家砌新屋后,爷爷奶奶就住在我家。在新屋,爷爷奶奶带着哥哥睡东边正屋,父母亲带着我睡西边正屋,两个姐姐睡东边靠后面的耳房。第二年,爷爷因高血压在我们的新屋里去世了,8岁的我看到爷爷静静地躺在床上,大人们忙进忙出,竟没觉得那是永别,只知道以后不用到对面山上扯玉米须给爷爷煮水喝了。 那时候,乡里经常有算命先生走动。一天放学后,我在上屋的伯伯家门口看到一个提着鸟笼子的算命先生,那只绿色的小鸟很听话,它的主人可以指挥它从一个装满纸签的竹筒里啄出一张来,再由算命先生解释给算命的人听,以预测他的命运。因为是小鸟啄出来的,大家都认为灵验。我在二伯母的怂恿下,也请算命先生让小鸟啄了一张。纸签上的内容让在场的人眼睛都亮了,都说我抽到了上上签,对我刮目相看,主要是因为两句话:金丝鲤鱼跳龙门,走得五条好运程。看到大家这样惊喜,我赶快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听了笑得合不拢嘴,肯定地说我会命好。 小学时候的我很强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和别的小孩吵架,在别人用高粱杆子捅了我之后,我将人家推到了路边的粪池里,在我跑回家之后,那家家长带着孩子来我家告状,从田里收工回来的妈妈压着怒火跟人家说对不住,人家一走,母亲就操着火钳朝我挥过来,打得并不重,因为母亲一身泥和汗,还要赶着去菜园摘菜准备晚饭,她没有时间教训我。但她警告我,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事,非打死我不可。好多年后,我跟母亲聊起这件事,母亲激动起来:细伢子之间一点点事情就来告状,这样的大人最不通礼,我是要做给人家看才装样子打你的。我们的一个邻居特别爱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孩子如何懂事,如何聪明。有一天在这位邻居走了之后,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大人看重子女要放在心里,不要放在嘴巴上。 不知道是因为砌新屋劳累过度,还是年轻时用眼过度,母亲在40岁上生了眼疾,几年时间里,到望城白马、医院等地方反复求医,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好在两个姐姐长大了,她们开始到队上出工。那时农村的中学教育抓得不紧,在“双抢”期间,姐姐们早晨天亮以前就下田扯秧,上午到学校上三节课,下午带着农具到学校,以便两节课后直接赶到白沙岭上参加挖红薯,晚上,她们就在一个山坳里做红砖。大姐姐做事手脚麻利又肯吃苦,一年下来,她挣到多个工分,竟然比一般的男劳力还多。 那些年,父亲一直在队上做农技工作,因为成绩突出,受到县市各级表彰,年还被海选为长沙县第八届人大代表。德才兼备的他一直被上级领导看重,有多次机会可以“提干”吃国家粮,但父亲没有脱离土地,他说:一家6口要吃饭,仅凭他一个人的工资养不活一家人。父亲还曾不止一次接受上级组织谈话,让他入党,他也没有入,爷爷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几十年中带来的纷扰让他心有余悸。 母亲喂了一辈子鸡鸭。照片摄于年。 六 年,长沙县开始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和我们家儿女初长成的条件一结合,能量大得惊人。分田的时候,我们家算6个半人(奶奶算半个),水田方面,按每人分1.2亩计算,加上折合面积,我们家共分得水田8.2亩,山林方面,按人均0.6亩计算,我们分得山林近4亩,菜地方面,按人均0.2亩计算,我们也分得菜地1亩余。这些田土对我们家来说,可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分田到户之后,父亲于年结束了在生产队兼任多年的农技工作,带着全家人,全力投入到发家致富的时代潮流中。 因为深谙农业技术,父亲是种田的好把式,我们家水稻亩产量比一般人家都高,年成好的时候,达到亩产千多斤。收割的时候,父亲带着4个子女下田,母亲在家里负责晒谷。我们先是全体割稻子,割倒一片稻子之后,两人割稻,两人脱谷,父亲专门挑谷回家。割禾的埋头苦干,脱谷的劲头十足,挑谷的健步如飞,晒谷的挥汗如雨,那种火热朝天的劳动场面让邻居乍舌,也成为我们难忘的记忆。 除种水稻之外,家里还种油菜,种西瓜,种花生,种玉米,栽橘树,栽桃树,制茶叶,养猪。原来家里养的都是黑猪,一年才出栏,后来改养良种白猪,三个月出栏。父亲种了很多红薯,不再是作口粮,而是拿来养猪。母亲每天早上到地里割几大捆红薯藤,挑回家,剁碎,煮熟喂猪。最多的时候,猪栏里有十几头肥猪,母亲系着大围裙,用大脸盆端猪食,用大木桶提猪食,一日三顿,每天在东边的厨房和西边的猪栏屋之间要打无数个来回。 几年之后,我们的家境在村上脱颖而出,手表、自行车、收录机、缝纫机、黑白电视机等高档商品,都较先进了我家。先一年,我还跑到山后的一户人家去看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第二年,我就在自己家里看洛杉矶奥运会。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围炉向火,父亲就将家里全年的收入做一个总结,当我们家年收入过万元的时候,全家人的心情喜悦到了极点。 年,父亲被选为长沙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五届代表。为推广农业技术,他为县植保站代销农药、农肥、种子,从84年至92年,这个工作持续了8年。那时候我们家每天人来人往,村民们在种田上有任何问题都来问父亲,下什么种,什么时候下,用什么药杀虫,什么时候杀,用什么肥,怎么用,父亲总是有问必答、热情指导。客人进门总要奉上一杯茶,母亲每天泡茶不赢。父亲还是一名兼职气象员。气象站就设在我家对门开阔的山坡上,每天要记录温度、湿度、风向、风力等等,哥哥姐姐都参与过这个工作,我因此也学到一些观察和判断天气的方法:久晴大雾雨,久雨大雾晴;斑鸠叫也有规律:早叫日头晚叫风,中午叫雷公。 父亲谙熟水稻种植技术。照片摄于年。 父亲的才学不仅体现在农业技术方面,青年时期对文艺产生的兴趣有增无减,80-90年代,他进行业余创作,在县市的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作品,多次获奖。年,父亲参加县里的文化工作,参与编辑了《长沙县谚语》一书。父亲的书法在本地也很出色,逢年过节,丧葬嫁娶,好多人来我们家请父亲写对联,从创作到书写,父亲一人包干,不是写一副,而是问人家家里有几个门,写一套,写完还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写,指导人家欣赏对联,说得来的人频频点头,心悦诚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乡镇企业也发展起来。黄花公社(后来改为黄花乡、黄花镇)出现了许多小型生产企业,到这些企业去当工人是当时的农村青年十分荣耀的事情。我的大姐高中毕业后进了玛钢厂,成了一名按作息制度上下班的工人。姐姐在花样年华进厂,和同样是高中毕业后进厂的姐夫自由恋爱,他们年结婚,年和年,接连生下了两个可爱的男孩。那时,家乡已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为了小儿子的出生,两口子上交了多元的罚款。姐姐姐夫虽然还是农业户口,但他们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家里的田都转包给了别人种。大姐两口子也是善于持家的人,他们在镇上买地,建起了两层楼房。他们教子有方,两个孩子都读了大学,如今都已经娶妻生子。姐姐姐夫辛勤一辈子,如今在家含饴弄孙。 二姐从小学习不错,但她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高中。父母亲给二姐设计的职业是做裁缝。当年,裁缝是一门较好的生计,父亲的妹妹孔再明就是裁缝,如果二姐跟着姑妈学习,手艺将会得到无保留的传授。虽然二姐心里非常羡慕大姐在工厂当工人,她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到姑姑家学徒去了。但三年后,学成的二姐终究没有独立从业,而是经人介绍对象,在年结婚了,同年生了一个女儿。二姐夫家在镇上有房子,两口子便开了一间五金店。那时,我正在位于镇上的长沙县六中读书,课余经常到姐姐那里玩。几年后,生意关门,姐姐搬回乡下,开始务农,姐夫则在外面“挣活泛钱”。由于夫妻聚少离多,生活观念不同,姐夫又不尽职养家,他们的婚姻以二姐年出走深圳而告终。二姐在深圳、长沙打工,漂泊多年,才于年重组家庭,新姐夫和原来的姐夫完全不一样,极勤快,极热心,对姐姐很好。如今,二姐已是两个小可爱的外婆。 由于长沙县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年轻人的出路多,我的家乡在八十年代并没有形成浓厚的读书跳农门的风气,倒是学手艺、学技术的人很多。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先辈代代务农,家族对年轻人读书深造没有太殷切的期望,总之,哥哥在初中毕业后,也没有继续升学。父亲给哥哥选择的职业是电工,哥哥一毕业就被父亲送到长沙一亲戚处学无线电,他手性很好,很快就会摆弄收音机等小家电。后来,哥哥又在乡镇企业学电工。现在,他已经在许多工厂工作过,始终没有离开电工岗位。哥哥年结婚,当年就做了爸爸,如今,哥嫂的独子也已经大学毕业,事业上进,爱情甜蜜,但哥嫂还在夜以继日的打拼生活,修路建房,忙得不亦乐乎。 作为子女中的老幺,我生而逢时,生活和学习条件比哥哥姐姐们优厚得多。父亲爱文化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小学起就开始看父亲订阅的《湖南群众文艺》《作品争鸣》等杂志,对《古今传奇》上登载的长篇小说《玉娇龙》等等非常着迷。年,我从东春中学初中毕业,考上了长沙县六中,这件事给家里带来很大的希望,因为我们村当年只有5个人考上高中。其实,我并不是同学中成绩最好的,有比我更优秀的同学考上了中专,提前“吃国家粮”去了。我年考上大学更是本地的一大新闻,家里终于出了一个读书的,父母亲极为高兴。 年对父母亲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他们在天命之年搞大手笔:家里建楼房。楼房就建在年砌的平房的前面,和平房相连,楼房住人,平房留作杂屋。率先建楼房,在本地十分抢眼,是父母亲一生创家业的标志性成果。建楼房听起来财大气粗,其实一砖一瓦都是血汗换来的。根据父亲事后的决算,新楼资产总计元,但父亲在建房之前手头上只有元现金,父亲找三位亲友借了一些钱,然后,从挖土制砖烧砖、挖泥做瓦烧瓦到平地、伐木、砌墙,除必要的技术活请人做之外,一家人事无巨细,亲历亲为。记得那时候没有电话,我不知道家里的情形,上大学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转了几趟车回家,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往家里扑,黑咕隆咚之中,竟然在屋门前掉进了一个土坑里,爬出来,借着屋里的灯光仔细看四周,才发现那是新楼的地基。 建好的新楼2层共计6间房。楼下3间,奶奶住一间,父母亲住一间,一间为客厅。楼上3间,哥哥在东头,我在西头,中间做客房。年正月,父母亲给哥哥办喜酒,嫂子进门后,很快生了侄儿。90年暑假,我回到家,把侄儿放在客厅的竹摇篮里,一边摇一边唱歌,逗他笑,哄他睡,感觉岁月无忧。 建于年的楼房,照片摄于年。 七 家运却像波浪,潮头连着波谷。父亲遭遇车祸,差点残废。父亲遭遇车祸是在年7月11日,他去乡上开会,走在酷热的马路边,后面一辆农用卡车上来,将他卷入了车底。性命垂危的父医院,大手术,住了48天。大热天,病房里住满了人,电风扇几乎没有效果,父亲个子大,每天躺在床上汗直流。母亲不停地给父亲扇风,出院的时候,那把新买的蒲扇已经破了。 父亲说:患难见真情。车祸的肇事司机家里很穷,赔不出医药费,父亲心软,自认倒霉,所有难处自己扛了。大姐家那时正在建房子,手头紧缺,拿不出多少钱。哥哥焦急地到亲戚家借医药费,舅舅们都说没钱,一圈下来竟一分没借到,伤心到落泪。关键时刻,又是伯父出手救弟弟。伯父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湘潭工作,他不仅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医院看望,送钱送物。父亲住院最受累的是母亲。医院,后来医院,医院陪了几个月,寝食俱差,担心害怕,晚上没地方睡,就睡在病房的地板上,贪了地上的湿气,也生了病,从那以后身体弱了很多。 年夏天的“双抢”让人记忆犹新。医院,侄儿才1岁多。我和哥哥嫂嫂白天在田里抢收抢插,晚上在屋后的晒谷坪收谷、车谷。夜里12点过,看着满天的星斗,心里想着睡在前屋楼上的侄儿会不会醒过来哭,医院里的父亲还能不能站起来,疲惫与焦灼无法形容。所幸的是,半年以后,生命力强大的父亲恢复得很好,家里重现祥和与生机。 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所有的孩子都立业了,按理说,父母亲拖家带口、养家糊口的担子可以卸了。他们应该退休,由我们四个子女来奉养,他们同辈的堂叔、堂伯们就是这样做的。但父母亲不愿休息,认为奶奶还在,他们要赡养奶奶,同时,他们觉得只要还能动,就要做事。那年,新湘村办起了一家纸箱厂,父亲在纸箱厂厂办工作,同时兼任村上的出纳。年5月15日,我的儿子临盆,医院陪产,悉心照顾,一切顺利,我产后第5天就回家了。因为父亲外面的事忙,家里离不开母亲,医院回了乡下。那年冬天,父亲被请去担任县农用车总厂办公室主任,一直干到99年7月份。他刚空下来了,离我家不远的正园门窗厂又来请,父亲在这家企业又工作了5年。 90年代父亲在企业打工。 在父亲在外打工的十多年里,哥哥嫂嫂也一直在外打工,家里完全靠母亲操持。年,母亲的右眼患白内障,逐渐看不见了。记得有次从学校回家,母亲哀伤地对我说,她会瞎了去。我躲到房里,偷偷哭了一场。所幸后来父亲设法让母亲做了白内障手术,才免除了失明之忧。年正月,85岁高龄的奶奶辞世了,父母亲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老人。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骨质增生、关节炎陆续在她身上暴露出来。年,她因骨质增生腿部疼痛到坐卧不宁,幸得当医生的姑爷用一种神奇的埋线方法解除了她的痛苦。年冬天,母亲在劳作中不慎摔倒,左手骨折,半年才愈。 八 考虑到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操持家务实在太辛苦,年12月,已经满了66岁的父亲终于决定结束打工生涯,辞职回家,他对别人说,要回家照顾婆婆子。母亲做了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恢复了,有一段时间特别爱看戏,湖南花鼓戏、黄梅戏、越剧都爱看,父亲就定期给母亲租碟子,附近音像店的戏曲碟几乎都在我们家放过。其实父亲回家,陪伴母亲只是一方面,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帮哥哥种田、种菜、搞柴,读书看报、栽树养花、创作诗联等等。父亲年加入长沙县碧湖诗社,每年都参加诗社的活动。在中国楹联协会、华夏书画院等机构举办的征文、征联活动中,父亲的作品频频获奖。 父亲在我家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乡村,属于能“主事”的人。他从26岁开始参与地方上的红白寿礼主持工作,孔家、刘家、方家的大事自不用说,其他人家的事也往往要请父亲到场策划和把关,一场事要忙两三天。择日子,定仪程,邀亲友,安席次,写婚书和喜联,写悼词和挽联,预算资金,登记礼簿,凡是父亲把关的,事情就办得井井有条,绝不会因为礼节上的不周到而让人说三道四。父亲出口成章,言辞典丽,主持过无数场婚礼,地方上的人说起他时都竖起大拇指,他却写了一副自嘲联:“号称文人,能说能写;诨名抹布,随用随丢。”因为名声在外,东家喊西家请,父亲特别忙,家里的事情有时候都顾不上,母亲难免埋怨,对他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快70岁了还在外面给人家“牵新娘子”。 父母亲同年同月生,他们的生日也就总是一起过,哪个的生日刚好碰上节假日,聚会就放在哪一天。年12月6日,父母亲迎来七十双寿,亲戚朋友都来祝贺,家里张灯结彩。父亲很高兴,写了一首词贴在大门边的墙上,是一首《踏莎行》: 戚友同欢,儿女共庆,古稀双满三生幸。年登七十不为奇,愧无业绩何劳敬; 人乐和谐,国施仁政,无忧衣食无忧病。喜今搭上末班车,夕阳不怅黄昏近。 父母亲七十大寿合影。 我们姊妹都各忙各事、各住各家,一年之中能够齐聚父母身边的时刻,也就是几个传统节日和父母的生日。每次回家,都可以品尝母亲做的美味,大快朵颐。记得年端午节,我和先生带着儿子下乡拜节,儿子说回外婆家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美味的姜炒肉片,老姜肉片是一道家常菜,可是母亲做的和我们自己平时做的就是不一样。饭后,我跟儿子做总结,外公外婆为了让我们回家能吃得过瘾,一直在精心准备: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干菌子,现在野生菌子又很难采到,所以外婆去年秋天就开始采菌子晾干;鸡也是去年开始养的;外婆大概在端午节前一个月就开始做咸蛋;红糖蒸蒜子是端午传统菜,外婆早三天开始剥大蒜子;外公早两天开始采药准备煮凉茶;至于买肉、点心、准备柴火之类的杂事就更多。真真是端午一餐饭,父母经年心。 年国庆节。 年8月,我公公八十大寿,从未到过隆回的父亲特意随我们夫妻赶到邵阳隆回祝寿,父亲撰写的祝寿联使得老屋充满了喜气。东门写的是“集萃留芳人文茂;中坚老旺世族辉。”联首嵌入了我公公的名字,横批是“松鹤延年”。西门写的是“同庆苍椿等耋寿;共欣慈竹报平安。”横批“南极星辉”。大门写的是“堂同四代千秋福;寿届八旬百岁春。”横批是一个大大的“寿”字。 我工作多年来,父母亲总是以我的工作至上,绝不肯因家里的事情让我分神,打电话问候,不到万不得已,他们都会说没事,没空不用回家。年秋天,因为事忙,我有两个多月没回家,心里惦记不已。有天发现下午有半天空,马上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一听说只是回去打一转,连饭都不在家吃,语气坚决不让我们回去,我说要看一下,她说有什么好看的呢,还不是跟平时一样的。我说我送给你看一下可以啵,母亲就笑。吃了中饭就出发,到家一进门,发现父亲早就给我们准备了几袋子红薯、凉薯、扁豆、黄豆、橘子、柚子什么的,母亲又带我到菜园,扯大蒜,割冬苋菜,砍白菜,掰莴苣,还给我准备了一大兜排菜潦了水做雪里红。在父母眼里,回家没吃饭大约等于没回家,所以母亲4点钟就开始做晚饭,结果吃了饭才5点。想着儿子放学要回家吃晚饭,我和先生匆匆赶回城里,儿子下楼接东西,看着摆了一地的袋子,他蹦出一句:你们是回去打劫的吗? 父亲种的菜。照片摄于年11月。 年,儿子上南京大学,南京是六朝古都,想着父亲爱看名山胜迹,我力邀父亲一同送儿子去南京。父亲非常高兴,到了南京,我们一起逛夫子庙,走总统府,看贡院,瞻中山陵。太阳很大,中山陵前的台阶很陡很高,父亲爬得很慢。晚上回到宾馆后,父亲说累,说下午是霸蛮爬上去的,膝关节很吃力。我才意识到,父亲74岁了,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挑着担子箭步如飞、举着酒杯豪气冲天、做什么事情都不在话下的汉子了。 年8月父亲随我们到南京游览 近些年来,父母亲本可以更轻松地安享晚年,但他们的日子伴随着母亲缠绵不断的病痛。年12月,母亲因肾医院,手术,石头打碎后取出来了,但肾脏功能衰退、积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年,母亲因左眼白内障,又做了一次眼部手术。年8月,母亲因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乡下多方求医未能缓解后,医院住了十多天。今年6月到7月,母亲因腰椎滑脱、腿痛难忍,两度入住解放军医院,做了手术,目前尚在康复中。除了多次住院,母亲每天都离不开药,胃药、脑血管药、口腔药、风湿病药,常年吃药吃得她胃口全无,饮食量很小,身体瘦到只有80多斤。父亲为治疗母亲的各种病痛,求验方,配中药,问医生,买西药,医院诊所十几家,到的药铺药房几十家,甚至于拜菩萨烧高香,办法都想尽了。父亲特别痛惜,好日子来了,母亲却没有好身体过。 年端午节。 今年,父母亲即将双双满79岁。我们这里的风俗,男做进,女做满,父亲应该在今年做80大寿,但父亲不同意,他要等明年,和母亲一起做岁,母亲则说明年也不做,最重要的要集中精力把今年的大事办好,把孙媳妇接进门。父母亲对他们能白头偕老感到很庆幸,他们说附近的人都讲廖家冲这地方神奇,好几对夫妇都是七老八十了,都还双双健在。 前几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弘扬廉洁文化: 上国昌廉政,群星拱北宸。 风清民意乐,气正党心淳。 屋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尘。 中华兴伟业,德教育斯人。 父亲胸怀社稷,我则想借父亲的韵,写我家风: 大义拥邦政,德孝教子宸。 严慈济和乐,化育情深淳。 乡村沐朗月,邻里亲光尘。 白手创家业,精神勉后人。 年春节四代同堂。 孔雀赞赏 长按让白癜风患者感受中科魅力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助力白斑圆梦征程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年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通联会在我市
- 下一篇文章: 新闻早知道今日看点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