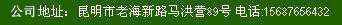|
北京看白癜风哪家比较好 http://m.39.net/pf/a_4661157.html “军人或记者, 包括医生, 你不能把它看作一种职业, 得把它看作一种事业。” ——白云龙 来湖南之前,白云龙曾是一名空降兵。在空军编制里,空降兵是一个奇袭的兵种,擅长突围,总在解围。 他所在的空降兵第15军,驻地就在湖北,白云龙和战友们的新兵训练也安排在这里。在这个离山东老家很远的省份,他度过了一段颇为难忘的时光,“我对湖北是有感情的”。 疫情发生后,湖南广电决定派记者前往湖北抗疫一线,白云龙提出了申请。因为湖北发生过几起记者感染事件,考虑到安全风险,新闻中心对这次采访十分慎重。经过向上级报备、详细评估和安全防护培训后,配备了防护物资的采访团队才向湖北进发。 湖北内外,天壤之别。 1月31日上午,湖南广电4人新闻团队出发前往黄冈,“路上车辆很少,只有少量的物资车拉着抗击疫情的物资往湖北方向走,昔日繁忙甚至堵车的高速上,变得荒凉。”白云龙在自己的采访手记中写道。 下高速进入黄冈,在防疫检查哨卡量体温、登记身份证、填电话号码,启程没多少距离又是一个检查哨,令人有些忐忑。 进入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湖南医医院4号楼,“5分钟的路程,每走一步,我都能感到自己的心脏跳得更快一些。” ▍疫情类报道的特别难度 重大事件发生地,向来是新闻高产地,疫情类报道却存在特别的难度。 首先,进入病房拍摄一般只能停留在清洁区,“污染区的危险度比较高,我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医疗队是不建议我们进去的。”防护物资又特别紧缺,“进去一次,就要浪费一套防护服。” 其次,不能耽误医生的工作时间,只能在下班后进行采访。湖南对口支援黄冈市5家医院,“一组4个人,不可能去所有地方。” 为了克服电视画面素材不足的问题,“很多时候要利用医生传过来的素材,就是他们拍的工作视频,我们再进行统稿。”白云龙介绍。 医院也有自己的规矩,比如,护士站的门后是半污染区,因为连接着污染区,这扇门是不能轻易推开的;即便要开,记者也要远离,让医务人员开。“动作不能太大,要慢慢地开。如果动作过大,会带动空气流动,带出病毒。” 又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虽被称为黄冈版“医院”,却是紧急改造而成。由于此医院,隔离区和清洁区之间只有一块玻璃,除了用玻璃胶密封,上面还贴着透明胶带。“相当于是临时建起的一座墙。”白云龙说,“如果你去拍,摄像机贴在上面轻轻一动,整面玻璃都在颤。” 对于拍摄面临的难题,白云龙并未与团队直说,而摄像出乎意料的解决方式却让他倍感惊喜。“白天去飞航拍,再怎么飞都是那4栋楼。但是晚上去飞,医院里都亮着灯,当无人机靠近楼宇时,镜头摇过去,所有病房里医护人员的工作情形我们全能拍到,当时真的感觉像捡到了宝。”后来,这些夜晚的航拍镜头,还被湖南卫视《元宵一家亲》特别节目采用了。 同样考验技术能力的时刻,是湖南后方临时接到通知,白岩松《新闻1+1》要与第一批湖南省援助武汉医疗队副领队朱华波紧急连线,因为湖南团队的4G包与央视的4G包信号不同,前方、后方与央视反复沟通、对接。“如果你仔细看那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前面还是电话连线,连着连着就出画面了,因为我们中间把线给连上了。” ▍从动态新闻到人物故事 与大多数电视新闻团队相似,湖南广电新闻报道团队也把本省所属的湖南医疗队行动作为报道重点之一。在黄冈,除了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湖南医疗队还进驻了黄冈市的红安、麻城、罗田、英山等县市。 报道团队奔走于这些地方,把镜头对准一线医务人员,先后播发了《本台记者走进黄冈“小汤山”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全力救治多名患者》《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治愈的首例患者出院》《湖南和山东共同支援黄冈:潇湘洙泗一脉相通》等报道。 抗击疫情期间,湖南广电按照“第一个调整综艺节目编排、第一个在黄金时段开辟疫情防控新闻专栏、第一个创制公益宣传片和主题MV、第一个举办‘抗疫’主题晚会的省级广电”“四个第一”要求,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报道。 新闻中心《湖南新闻联播》《午间新闻》《新闻大求真》《新闻当事人》《平民英雄》、芒果云客户端推出抗击疫情专题板块,湖南卫视“”档制作了特别节目《抗击疫情特别时间》。 团队在黄冈的采访中,发掘了很多动人故事。 前几日,来自株洲的护士朱娟玲迎来49岁生日,是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护士。疫情期间,黄冈市社会福医院,条件相对艰苦,一时请不到护工,朱娟玲及同事们还要承担端茶送水、清洁打扫的工作。 在核酸试剂供应不足、众多疑似病例担惊受怕时,医护人员还要主动为病人疏导心理。有的病人情绪波动大,有时会闹、会抓人,动作稍微大一点,拉扯一下防护服、手套,医护人员立马就面临职业暴露的风险。 被指定为护理长的朱娟玲用行动带好头,成了这支年轻医护团队的主心骨。她申请来疫区的理由让白云龙感动,“因为丈夫也是医生,别人来医疗队可能会有家人不理解的情况,但因为夫妻是同行,所以他们之间从来不用过多解释,从结婚那一刻起,彼此心里就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朱娟玲觉得这是她的优势。” ▍做好防护,积极应对 对家人,白云龙最初采取的态度是半瞒着,“自己做过哪条新闻、哪个稿子自己都忘了,但爸妈永远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去了哪些地方,他们天天守着看。我爸妈就比我还了解湖南的天气预报。” 出发去湖北前,他只向父亲透露了实情,并请他暂时对母亲保密,最后还不忘嘱咐“最近不要看湖南卫视了,省得露馅”。 来到黄冈,团队不是没有怕过。一位年轻的女护士,虽然防护得严严实实,可在半污染区交接工作时,还是有消毒剂洒进眼睛了,“真的把她吓得够呛,不知道怎么弄。其实来到这儿的医护人员不全是感染科的,有呼吸科的,还有别的科室紧急征调过来的。” 恐惧、担忧甚至把疫情当作洪水猛兽,在白云龙看来,都是因为对病毒不了解。第一次进入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医疗队长就告诉他们,只要按正确的规定做好防护就一定没问题。“后面我们慢慢地了解了,”他说,“人有时候纯粹是自己把自己给吓的。” 做好防护、积极应对。白云龙和一同赴黄冈采访的同事记者吴玉、摄像李银、杨帆,驾驶员郭正华、胡亚曦之间渐渐形成了默契(团队中间进行了两次轮换,但白云龙都申请留下来)。 比如,互相只讲鼓劲的话、不讲泄气的话,互相提醒防护和消毒的正确步骤,不谈论网上的谣言,“你越讲大家越怕,人越怕、越胆小就越容易出事。” 在了解病毒、做好报道的同时,白云龙已经可以“科普”“辟谣”了。他提到,医护人员把塑料袋套在脚上以及用垃圾袋自制防护服的报道,“里面是有脚套的,再套一层塑料袋是为了多一层防护;自制防护服也是同样道理,大家都是理性的人,不可能说披个塑料袋就冲进去了。” 还有医护人员一天在病房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的报道,“不排除有这种极个别的现象,但后期防护物资紧缺情况慢慢得到缓解,现在6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来了,往后甚至可能缩短为4个小时轮一班。”关于公共交通封锁后医生护士步行上班的报道,“我们跟医疗队还有医生都聊了一下,这种情况不在少数,不过确实没必要过度渲染。” ▍“伟大都是逼出来的” 每一次拍摄,用过的设备都要用酒精擦拭一遍。第一次拍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没拿到审批之前,团队只能用无人机在外面拍。“无人机也一样,回来要消毒。很多电子产品喷酒精还容易短路,多次擦拭后,我们有一台上面已经有了黑斑。” 当酒精也没有的时候,只能用84消毒液。白云龙笑言,“我现在裤子上全部是斑斑点点,跟星空迷彩似的。”他不准备扔掉它们,“留着作纪念,挺好的。” 白云龙说,回湖南后,他最想的是能买点肉给自己做一顿大餐。很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山东人在年节中“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习惯。 不过,他最喜欢自己做的一道菜,是清炒苦瓜。“原来我不喜欢吃苦瓜,但在部队的时候吃大锅饭,有时候第一批战友打完了,你再去盛菜的时候,留下最多的就是苦瓜,慢慢地越吃越觉得口感还蛮不错的。” 白云龙本科就读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他恰好赶上湖南广电新闻中心的一次特殊招聘:年马航事件后,新闻中心有意招收更多理工科学生,以丰富记者队伍的知识结构。“同一批还有学体育的,最初台里还准备招两个学刑侦的。”他对记者说。年,他进入湖南广电新闻中心,正式成为一名电视记者。 “军人或记者,包括医生,你不能把它看作一种职业,得把它看作一种事业。它让你感觉能为别人去做一点事情,就像男孩子小时候看奥特曼,内心总会生出一个英雄梦。” 年初的这场疫情中,媒体之间的新闻战也顺势打响:谁更贴近一线,谁更有能力做出好报道,全在公众的眼皮子底下。白云龙也会经常学习央视或其他同行的报道,“其实这个时候,能站出来的媒体都不是孬种。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及时、全面、准确的信息。”在采访的前一天,他看了一篇文章,上面写着“伟大都是逼出来的”。 他觉得,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害怕和担忧都是人之常情,医院,进入工作状态,“可能连30分钟都不用,只要机器一架,开始拍了,你就会发现心静下来了。” 他想起做空降兵的日子,“登机之前那种等待是你内心最忐忑不安的时候,等登上飞机,你只会想着怎么去完成任务,心里就真的一点恐惧都没有了。” (本文转载自“广电独家”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招聘湖南省新田县消防救援大队湖南省襄阳
- 下一篇文章: 重磅刚刚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5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