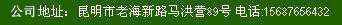|
杨际平,男,年9月出生,福建平潭人。—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先后在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湖南零陵三中、零陵一中工作。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年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隋唐两宋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敦煌学研究。历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出版专著三卷本《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以下简称《史论集》)《均田制新探》、《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前者的增订本)、《中国财政通史》(秦汉卷),主持编著《中国经济通史》第四卷(隋唐五代卷)、《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参加编写《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韩国磐先生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郑学檬主编)、《简明中国经济通史》(郑学檬主编)。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本文原载《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出土文书研究卷》,厦门大学出版社,年。) 毛蕾 杨先生,您好,首先恭喜您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唐宋卷》、《出土文书研究卷》,收录了您各个时期共篇论文,基本上涵盖了您所有的研究成果,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套论文集的出版缘起? 厦大历史系鲁西奇教授担任厦大系主任期间,在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的资助下,将这套论文集列入了“人群·国家·社会”书系的出版计划,把我散在各处的论文结集出版,也算是对我个人三十多年学术研究的总结,非常感谢。 杨际平 (《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 毛蕾 杨先生,您是我们尊敬的学界前辈,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有突出成就,就从这套书每卷的标题也可以看出,您的研究领域跨度很大,从秦汉魏晋、隋唐五代乃至延续到两宋。能否请您简单谈谈您是如何走上从事历史研究这条道路,是怎样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呢? 我高中是在福建师院附中(现为福建师大附中)就读,当时不分文科理科,我的兴趣很广泛,各科成绩也都比较均衡。并没有对历史课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只是有一次历史课的课外活动,写过一篇习作《李密与瓦岗军》。虽然用的都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但毕竟是一次大胆尝试,不知道这算不算冥冥中我与隋唐史的缘分。 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北大历来有各种学派“兼容并包”的传统,学生与老师有不同意见很正常,老师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回想起我这几十年的学术经历,北大这种开放、严谨和鼓励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是对我影响最大的。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工作2年,后在零陵中学当了15年中学教员。 业余时间,我就中国古代史的一些问题写过几篇论文。“文革”期间完成的几篇学术性文章,一篇是《释“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刊在《历史研究》年第1期。一篇是《私田制即封建制说质疑》,刊在《福建师大学报》年第1期。还有一篇是《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几个问题的探讨》,就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途径等问题提出与郭沫若先生不同的看法,认为井田制不等于奴隶制,私田制不等于封建制,不能在诸侯公室与卿大夫私门之间划分阶级;中外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暴力革命夺权的事例。当时完稿后曾寄给北大周一良老师,征求意见。周一良先生把它推荐给《历史研究》,但终无下文。后来在我考上厦大研究生后才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年第4期。 年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有幸以不惑之年考上厦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师从韩国磐先生。既实现了我希望回到福建原籍的愿望,又能从事历史研究,可谓一举两得。当时招收的研究生不多,大家都很珍惜这一机会。社会经济史是厦大历史系的强项,在这样的氛围里,厦大历史系最初几届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论文选题不约而同都是社会经济史,我自然也不例外。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图书馆看到《敦煌资料》第1辑,便深深地被它所吸引,直觉告诉我,这是研究北朝隋唐经济史、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实施状况的绝好资料,从此我便一头扎进去,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汉唐经济史便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韩国磐先生对此也十分认可,我的硕士论文便定为《略论均田制的几个问题》。后来逐渐延伸到汉唐土地制度,再延伸至赋役制度、户口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农业、阶级阶层关系(如奴婢问题、雇佣关系等)、社会生活(如家庭宗族关系、婚姻制度、社邑活动)等,研究的时限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主,有时也延伸到秦汉、两宋(仅限于土地制度)。所利用的出土文书也由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扩展至秦汉三国简牍。总的来说,结合出土文书研究均田制实施状况始终是我的主要研究课题,并逐渐扩展到汉唐经济史研究。研究范围相对集中,彼此间有一定联系。 杨际平 毛蕾 您在从事中学教学的15年间,研究环境和研究条件应该都十分有限,但您完成的这几篇学术论文质量都比较高,而且已经显现出您不盲从权威、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研究特点。您刚才也提到,您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主要是侧重于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秦简、汉魏简牍等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相印证,我们看到最新出版的《史论集》中也专列了一卷《出土文书研究卷》。请您具体谈一谈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出土文献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利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时应如何平衡? (《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出土文书研究卷》) 我以为就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是两条腿走路的关系,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相得益彰。比如说,传世文献中有关政治史的资料相对较多,出土文书则相反,有关政治史的资料相对较少,而有关社会史、经济史的资料就很多,并且很具体;传世文献有关州郡以上层级和社会上层的资料多,反映乡里基层与社会下层的资料少,出土文书则相反,基本上都是反映乡里基层与社会下层的资料;还有,传世文献(特别是正史),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较多,关于这些制度的实施状况的资料很少。出土文书又恰好相反。这些方面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正好形成了互相补充的关系。 出土文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原始的实证资料。与传世文献不同,出土文献除了一些墓志和碑刻,都是无意中留传下来的,比如敦煌吐鲁番资料、里耶秦简、走马楼三国吴简,都是当时废弃的官、私文书,这类出土文献记录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原始状态,从资料的可靠性方面来讲,出土资料往往是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但出土文书往往残缺不全,背景不明,如果对传世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典章制度)不熟悉,就很难宏观把握,准确应用,充分发挥其史料价值。所以,也不能孤立地研究出土文书。必须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这样资料就比较齐备、完整了。 我举一个例子吧。以前对秦汉时期、魏晋时期,奴婢是否登记入户籍是有争议的。有些学者据《唐律疏议》“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认为奴婢既是作为主人的财产,视同牲口,就不会登到户口册上。但里耶秦简、走马楼三国吴简都确切证明了当时财产不入籍,而奴婢是入籍的,登记在老百姓的家口之后。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实证资料的佐证,就很难取得共识。 (走马楼三国吴简) 再比如秦汉乡里与邮亭的关系问题。史书在这方面记载都很简略,并且有很多矛盾。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县辖乡,乡辖亭,亭辖里。亭“是统辖里的一级政权”。一种意见认为长不主民事,乡不辖亭,亭不辖里。这两种意见长期争讼,达不成共识。直到东海郡尹湾汉简的出土,才一举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东海郡集簿》中,“乡”与“里”单独一行,上承县、邑、侯国。“亭”与“邮”也单独一行,独立于“乡”、“里”之外。显示“乡”、“里”与“亭”、“邮”属于不同的系统。 从这些例证都可以看出,出土文书对于社会经济史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基层社会的生产、生活状况是何等的重要。至于说在研究过程中,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二者如何平衡,那得依所论的内容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杨际平 毛蕾 您关于出土文书和传世文献两条腿走路的说法,与您强调要北京治疗白癜风医院在哪里点滴状白癜风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国家环保部赴湖南湘潭调研土壤污染治理工作
- 下一篇文章: 株洲污水直排湘江威胁下游饮水安全恳请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