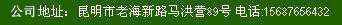|
�����ɽ:����ɫɫ���й��ŵ�ͼ ��˵�е��й��ŵ�ͼ��Դ���磬����ǧ����ǰ���Ѿ���ʹ���ˡ��ڴ�Լ��Ԫǰ21���͵��ij�����һ���Ӳ���ͼ�������£�˵���Ǵ�����ˮʱ,����Ӳ���һ��ʯ�ڴ�����������ˮ�õĵ�ͼ����������ָ����ˮ�����ڳɹ����˴�˵������ͼ����������������� ��Ԫǰ����ʼ�ʵۼ�λʱ��������ȫ�����еĵ�ͼ�ռ���������ʱ�ĵ�ͼ��Ҫ�DZ�ʾ������ͼ�ľ��µ�ͼ������������ʱ������������ǣ���Ԫ�꣩ʱ�����������ε�һ���¾������˾������Щ��ͼ���չ������Ա�����Ϊ������ͳ�����á� ����Ҫ˵�й��ĵ�ͼ��ʲôʱ��ʼ���֣��������ڴ���ս��֮ǰ�����ˣ�����ս�������ս�²��ϣ��������õ�ͼָ��ս������ͼ���ǵõ���ʵ�����á�����ʱ�������ж����ˣ��ɼ��й���ͼ�ij���֮�硣�������ĩ�Ӻӱ�ʡƽɽ��ս��ʱ��һ������ĵع��г���������ͼ�������������ʷ����ר�Ҽ���Ϊ����������ĵ�ͼ����ͼ�ϵ����־����й��Ŵ�ս��ʱ�ڵ����֡����ġ���д�� �������ȫͼ�������Ү�ջ�Ĵ���ʿ��������й�����ʱ�����Ƶ������ͼ���ǹ����ִ�����ġ�Ҳ��Ψһ��һ���ݿ̱�ġ��������ͼ�� ��Բ�ط�:�ŵ�ͼ����α�ʾ�����鿴��ͼʱ��DZ��ʶ��������ǣ���ͼͨ�����Ա�Ϊ�Ϸ�������DZ��ʶ�����ڵ�ͼ�Ļ��ƹ����ǣ�����������������ֹ���Դ�ںδ�?Ϊʲô��һ�����Զ���������������Ϊ�Ϸ���?���ٶ�����ǰ�������й���ŷ�ޣ�������˹�����磬��ͼѧ�һ��Ƶ�ͼ�ķ�λ�����ڸ��Ե��ڽ������������dz�ݵķ���ȴ������ͬ�� Դ�ڴ�ͳ�Ļ����й��Ŵ���ͼѧ��13�����Ѿ��γ����Ա�Ϊ�ϵĵ�ͼ�淶�����й��Ŵ���ͼʦ�ձ�������һ�淶ʱ��ŷ������Ȼ�ϸ����ѭ���Զ�Ϊ�ϵĻ�ͼԭ����˹����ͼʦ�������Ϸ���Ϊ��ͼ���Ϸ��� ��14���Ϳ�ʼ��ŷ���˺���˹���˻��������ͼ�ķ�λ������ʵ���Ա仯�����������̻���˹���̵ĵ�ͼѧ���Dz�Լ��ͬ�ط����˸�����Ϯǧ��֮�õĹ������������Ա�Ϊ�ϵĻ�ͼԭ�����ۻ�����ͽ������˹����ͽ���ı��������ڽ�����������ص�ǧ��ϰ�ߣ����Բ���һ��Ѱ�������顣 �ɶ��칤:�й��Ŵ��ĵ�ͼѧ����˵�е��й��ŵ�ͼ��Դ���磬��ǧ��ǰ���Ѿ���ʹ���ˡ�����ʱ����ͼ�ѱ��㷺��Ӧ�������������¡����н��輰Ĺ��滮�ȷ��棻�Ӵ���ս�����غ���������֮����ս���ϣ��Ե�ͼ����Ҫ��Խ��Խ�ߣ�ʹ��ͼ���Ƶ�ˮƽ�������ԵĽ��������������ķ�չ������������ͼ��������ͼ�������нϴ���ߣ���ͼ������Ҳ�нϴ�ͻ�ơ�����������У�һЩ�����ڿ�ѧ̽���Ĺ��˷�������Ҫ�����á� ���㣨-�����й��Ŵ���ʱ���ĵ�ͼѧ�ң�������ʱ������Ż����ڣ���ý������ʶ���ԡ���Ϊ˾�գ��൱�����ࣩ�������ڹ�������֮�࣬��ܻ��ڡ���ͼ�����μӹ��о���ս���о������µ�ͼ�ı��ƣ��˽��ͼ��ȷ�ȵ���Ҫ�ԡ���ǰ�˾���Ļ����ϣ�����˻��Ƶ�ͼ�������ص�����ԭ������ͼ���塱�� ����ͼ֮�������ɡ�һԻ���ʣ����Ա����֮��Ҳ����Ի�����������˴�֮��Ҳ����Ի������Զ�����֮��Ҳ����Ի����,��Ի��а����Ի��ֱ,�����߸���ض����ˣ�����У����֮��Ҳ����ͼ������ʣ���������Զ��֮��з��ʶ����������֮��һ�磬��ʧ֮�������������������ʩ��ɽ������֮�أ���������ͨ���е�������¡���а����ֱ֮У����·֮������Զ��֮ʵ��Υ��ʧ��֮���ӣ����Դ����߲ζ���֮��ȻԶ��֮ʵ���ڷ��ʣ��˴�֮ʵ����������·֮ʵ���ڵ������֮ʵ���ڸ��¡���а����ֱ֮�㡣�����о�ɽ�Һ�֮���������֮ⷽ�ģ��ǽ�����֮�Կɵþٶ����ߡ���֮������������ֱԶ������������Ҳ��������������ͼ�����ԡ� �������ݡ���ͼ���塱���ۻ����������ġ���������ͼ����ʮ�˷���ͼ�ϲ�������������ص�����������ص�λ�ã����ҰѹŴ��ľ��ݡ���ʷ�ϸ������������л���Ļ�ַ��ǩ����Լ�ĵص㡢�ŵ����Ա�ʾ��������һ���������ҹ��Ŵ���ͼ����ѧ����Լɪ����Ϊ���й���ѧ��ͼѧ֮��������ŷ��ϣ��������ͼѧ�������ܣ�PtolemaeusClaudius��Լ��Ԫ90-��������������Ŵ���ͼѧʷ�϶�����ӳ�����Ų������ǡ� ʷ������:�й��ŵ�ͼ֮���й��Ĺŵ�ͼ��������Դ���л��������ڵ��Ĵ��������������ĹŴ���ͼȴΪ�����٣���Ϊ��ͼ���������ԡ��Ŵ���ͼ���ʵIJ��ױ����Լ���ͼ�����ĸ����Զ�Ӱ�������Ĵ�������˽��������ܿ����ĹŴ���ͼʵ���Ƿdz��ٵģ����еġ�֮������Ե����������.��12���ں��ϳ�ɳ�����Ѻ�Ĺ������פ��ͼ����Ŀǰ���ֵ�����ľ��µ�ͼ��Ҳ������IJ�ɫ��ͼ��ͼ�з������ߡ����µص�������ɫ��ʾ���������˹���ˮ����������ɫ��ʾ��ˮ�Ӽ�������ú�ɫ��ʾ�� �����ִ������ӡˢ��ͼ���θ������������ױ�������ͼ���еġ�ʮ��������֮ͼ�����Ƽ�ʷר����Լɪ˵����ŷ�ĵ�һ��ӡˢ�ĵ�ͼҪ�����������ҡ���������ˣ���ͼ��ͼˮƽҲԶ��ŷ��һ��ӡˢ��ͼ֮�ϡ� ��������ʵ���֯���ġ�����ȫ��ͼ�������й���һ��ʵ���ͼ�����۴���ѧ������ʵʩ�����Ĺ�ģ֮���ʱ��֮�磬���Ǵӵ�ͼ���ݵ��꾡�̶ȺͲ�ɫ�滭ˮƽ�����������й��������ͼѧʷ�ϼ�Ϊ���ĵ�ͼ��Ʒ���˺�������ĵ�ͼ���Դ�ͼΪ�����������ز�ͼʱ������������������壨������ȫ��ͼ���ϱ���Ϊ����ĸ�������֡���ϵ���Ů������塱������)����ӡ�Ȳ����ֵ�Ӣ������Ա������˹��G.Everest�����̷���꣨�꣩�Դ˷�IJ��Ҫ���ꡣ�Ƽ�ʷר����Լɪ��Ϊ����ͼ������������Ҳ�ǵ�ʱ���������е�ͼ���ȷ�ġ� ����֮��:��ͼ�ϵ�˼��ʷ�ڲ�ͬ�ĵ�ͼ�Ϲ۲�Ŵ��й�������۵ı仯���Ǻ���Ȥ�����飬��Ϊ���ֵ�������geographicalimagination��ʵ������һ�ֹ������κ������������������������ʷ�������źܶ�������ʷ�� �Ͼ���ͼ�����˻��ģ����Ƶ�ͼ��������������û��������֮�䣬��������˵�˼·�����档���ӽ�ͨ�ģ����Ե�·���������������ĹŽ��ظ�ģ������������Գ���ذ��ı仯�����ҵĵ�ͼע����dz���λ������֮���ڣ������ߵĵ�ͼ���ĵ�ȴ�����ξ����shopping�ص㡣 ���ĺͱ�Ե ������ͼ���״λ��Ƴ���������������ͼ���ڵ�ͼ���й�λ����������ġ� �ر�����������������ģ��ǵ�ͼ���Ӿ����������Եλ�ð��š����ĺͱ�Ե��ʵ���ϲ�����һ������λ�õ����⣬����Ҳ���ڷֱ��ֵ�IJ��죬������ȷ�ϡ����ҡ��롱���ߡ��������оͳ��������������ӣ����統����˵������ˡ���ʱ����������ʶ�ذ��Լ���λΪ�������ˡ��ģ����������ˡ��ı��������д˵�Ϊ���ĵ���ζ�ģ�����������˵����ʡ�ˡ��������˵�����С���������˵�������һ���� �ڵ�ͼ�ϵĴ�С������ȴ���и����˼��ʷ���壬����˵���δ��ġ�����ͼ����������ͼ�������ߵ�ͼ���ڻ������������ձ������ȵȣ����ử�ú�С��������Ǭ�����ȫͼ�Ž������¼����������¾ű߷�Ұ�˼�·��ȫͼ����Ҳ��������֪����������Ժ���Ȼ�Ѹ�����˵�Ĺ��һ��ú���һ������С�������ְ�����Ȼ���쳯����������������ڡ� ��ѧ�����ձ���Ϊ��һ�������ˡ����ġ�����������ڡ�孻�־�ԡ����ĵ�ͼ�У���Ȼ���й����÷·�ռ�������ޡ� ���� ����北京市中科医院好不好北京什么医院治疗白癜风
|
------�ָ���----------------------------
- ��һƪ���£� �ڲ���ͼ������܊���Ͽɲ����й���������
- ��һƪ���£� �ذ������������µ�����ǣ������Ӱ�¼���
- �ȵ�����